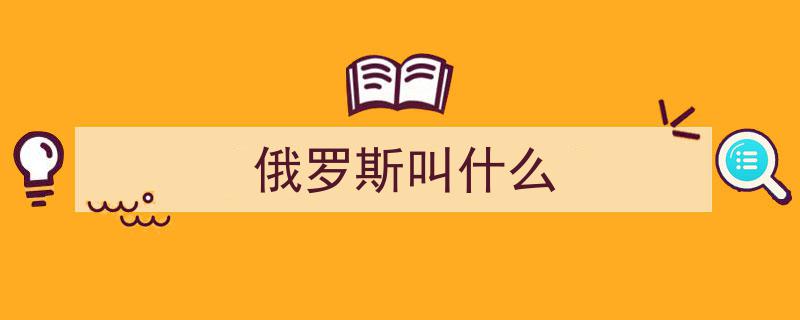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中国人民对于那些和我们亲密的国家也是有着自己的称呼,例如巴勒斯坦为巴铁,俄罗斯因为其彪悍的民族风格,也是被我们给予“战斗民族”的称号。
而俄罗斯给予我们的称号,并没有像英语那样用青花瓷“china”代指中国,而是称中国为“Kitay”,翻译过来就是契丹的意思,这两个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并不陌生,但为何俄罗斯用契丹来叫我们呢?

先抛个小场景。冬天的莫斯科地铁里,风一股脑儿往人脖子里灌。车厢里两个大爷聊天,“基泰?”“基泰!”他们指着手机里的红旗说话。我那时第一次意识到,俄罗斯人嘴里的中国,不是“China”,是“Kitay”。这词像老硬币,边缘磨得圆滑,却还带着骑马的腥风味儿。为什么偏偏是它?要说“战斗民族”是我们给人家的外号,那他们给我们的“回礼”,竟是一段一千年的旧事。
话得倒回去。从北方草原的一阵马铃开始。公元十世纪初,一个名叫耶律阿保机的人把散碎的部族捏成一个拳头——契丹。从此北方不再是边角料,而是一个有规矩、有军马、有自己说话方式的强权。后来他们改国号为辽。四周的人怎么叫他们?蒙古草原的人、汴梁城里的人、女真新贵,都喊“契丹”。一个称呼喊久了,反而比年号更稳定,像刻在鞍桥上的刻痕,哪怕换了马,还在。

辽被金打翻在地,这是1125年的事。可这个民族的脚步没停。耶律大石带着一群不服气的贵族和军户,往西,走得很远,走到沙与雪相交的那片地方——中亚。他们在那里立了一个新家,史书里叫西辽,别人也叫“黑契丹”。你想啊,第一次走到异乡,别人问“你们从哪儿来”,他们大概也干脆:“契丹”。于是这两个字,就被驼队、关市、驿站一点点带着走,沿着草原丝路往西爬。
名字的魔力在这儿。西域人见着丝绸、茶砖、纸墨,见着来自东方的硬货,统统往“契丹”这筐里装。后来你在中亚、西亚的旧书里,能遇到浓得发黑的词儿——“契丹雪”指火药,“契丹芦荟”说的是大黄。听上去像江湖上的暗语,其实不过是见物识人:东西来自那个叫“契丹”的地方。

真正把这词推到更远的,是蒙古人的马。成吉思汗那一脉,往西走三回,铁蹄踏过中亚、西亚,连东欧也落了他们的旗影。蒙古人早年习惯叫北方那片国度“契丹”,后来辽亡,金兴,他们干脆把“契丹”这个外号盖在金头上,再往后,干脆说整个汉地都是“契丹”。名字在他们嘴里,不拘一格,但有个意思一直没变:东方强国,那个能出丝绸和硬骨头的地方。
你再看北方的罗斯诸公国。当年他们像一肩挑的扁担,左边是森林,右边是河网,各自为政。等到十三世纪末,拔都领着第三次西征的军队过来,基辅、弗拉基米尔这些名字,瞬间跟火光绑到一起。两百多年,蒙古人在上面收汗血马、收银子,收服脾气。语言也顺带过去一些。税、军、驿、站,不光是制度,更是话里的痕迹。“Kitay”就是这么混进了俄语,与冬天的风一起,吹进了炉火间。

我后来在莫斯科瞎逛,还专门去看了“基泰城”(Kitay-gorod)的地铁站。有人说这“基泰”并不指中国,原意像竹篾编的城墙;也有人懒得考据,笑说:“这不就是中国城吗。”对不对,老百姓不那么计较。一个词活在城市里,会自己找解释。对普通人来说,Kitay就是东方,是瓷器、茶叶和火药的混合味道,是遥远而真实的邻居。
当然,别忘了书这种东西的威力。十四世纪初,有个从伊比利亚出发的使者一路晃到撒马尔罕,见帖木儿。他的行记里,提到东方的大使,一口一个“Katay”。欧洲读书人就这么接触到“Cathay”,后来传来传去,变成不同的拼法。但意思没变:远东的那个大国。再加上后来更出圈的马可波罗,他做买卖时通蒙古话、波斯话,到了写书的时候,干脆用他熟的舌头,把东方写成“Kitaia”“Cathay”。他笔下的草原驿站、杭州丝市、忽必烈的帐廷,在西欧掀起了漫长的好奇心。你要说这书哪里不靠谱,那另说;但“Cathay”这个音,像一缕烟,从他卷宗里飘进了许多人的耳朵。等到莫斯科公国向西看、向西学的时候,这股风也灌了进来。

有人会说,那1480年以后,伊凡三世把金帐汗国的影子赶走了,俄国不再受蒙古节制,那“Kitay”这口音应当淡了才对。偏没。词这东西怪就怪在,它不跟政权对表,只跟记忆混个脸熟。你想,两百年的听觉习惯,路上遇见的中亚商队、南边渡来的丝绸、北地市集上买到的茶饼,都是“契丹”的刻章。再有西方书本上“Cathay”的冷香一熏,这个称呼在俄语里就坐稳了。中国叫“Китай”,中国人叫“китаец”。你要是跟他们说“Weare China”,他们点头;你说“мы из Китая”,他们眼里一亮,嗯,懂了。
顺便再说句“战斗民族”。咱们喜欢这么叫他们,多少是看着历史里冷气直往外冒:冰原、伏特加、拿破仑、库尔斯克、列宁格勒,性格的棱角被冬天打磨得硬邦邦的。可他们给我们的“Kitay”,里面不是战吗?也有,是成吉思汗铁骑带来的震动,是草原风与中原器物交错的回声。但更多的,是生意、是市井、是沿街驼铃和狼烟之外的往来。称呼是战后留下的和平语言,这话一点不玄。

把故事拎回最初的“契丹”。这个民族在北方存身两百年,变成一种稳固的印象。辽亡后,耶律大石那一拨人继续往西,把“契丹”当成一面游动的旗,插在陌生的山谷里。再之后,蒙古人把这面旗变成路标,挂到四大汗国,同一时间,它又被欧洲游记捡起来,塞进欧洲人的地图。最后,这旗落在了俄语里,不再猎猎作响,却成了一个平常不过的名词。你看,多像一个人的命运:先烈火,再余温,最后归于寻常,日复一日地被叫出声。
有些细节我很喜欢。比如中亚人把火药叫“契丹雪”,多形象;又比如俄罗斯街头大爷喊“китайскиеогурцы”(中国黄瓜),那个“китайские”的尾音往上挑,调子里没有距离。还有一次在伊尔库茨克的旅店,老板娘问我从哪来,我说“中国”。她犹豫了一下,又笑着确认:“Kitay?”我点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名字不是地图的注脚,是人和人之间找到的一条捷径。她不用知道契丹是谁,辽在哪儿,西辽又在哪儿,她只需要确认:你从东方来。

所以,俄罗斯人为什么叫我们“Kitay”?因为最先传到他们耳朵里的、跨过草原、驮着丝绸和马鬃的,是“契丹”;因为蒙古时代形成的叫法顽固得很;因为后来书本、商路和邻里相处,把它固定成了日常。名字有惯性。英语抱着“China”,俄语揣着“Kitay”,两种习惯,一样真切。
故事讲到这儿,也不用非得收个整齐的尾。等你有一天在莫斯科的雪夜里抬头,看到红色城墙后面那圈儿光,或者在哈萨克草原上听一阵风吹过,Kitay这个音会自己浮起来。它像一条很长很长的河,起点在北方骑兵的马镫旁,绕过许多人的生活,最后流进别人对我们的称呼里。我们常说,名字里有命运。那不禁要问一句:在我们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些叫惯了的词,也早已走失了它原来的来处?我们叫得自在,名字在风里回头,谁又知道它曾走过多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