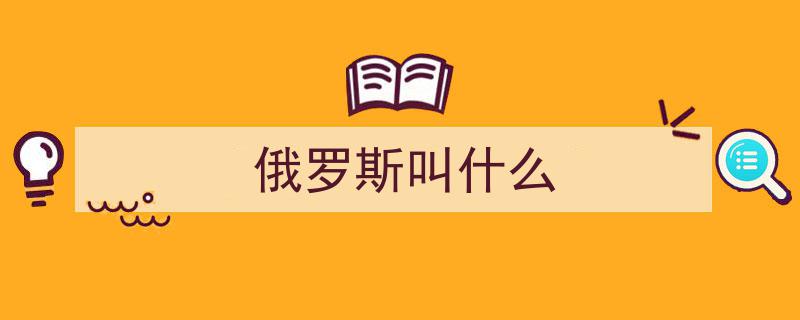被叫作“契丹”的中国:名字背后的风沙与马蹄声

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我们给朋友爱起外号,叫着叫着就亲了。可轮到别人给我们起外号,心里多少会有点别扭——俄罗斯人见到中国,张口就是“Kitay”。叫得这么顺口,却是一个千年前的旧名:契丹。

说起来,我们平时也不客气。巴勒斯坦喊“巴铁”,俄罗斯喊“战斗民族”,这些个称呼像是茶桌上的玩笑话,听多了就成了习惯。可“Kitay”跟“China”又不一样,它不是瓷器,不是青花盘,而是从草原上长出来的一个名号,骑着马、带着风沙,跑了很远很远才停在莫斯科的口舌里。
你要是去过俄罗斯,走在街面,跟人讨价还价,听到“Китай”那一声,真有种旧词从历史里冒出来的感觉。头一回听见的朋友会懵:“我们怎么成了契丹?”其实这事儿没什么阴谋,是一个名字在另一条路上活了下来。

往回翻,得从草原上讲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北方升旗,契丹人把散乱的部族拢了起来。辽王朝就这么立住了。那时候北方冷,旷野大,辽与宋在版图上推推搡搡,一南一北,各自过日子。边界的集市里,商人互相叫对方“契丹人”“宋人”,没人会在意词的将来。名称嘛,当时敲定的就是“契丹”,久而久之,辽也被这两个字贴了标签。
这段对峙,不是只有刀兵。还有婚书、公主和贡马,甚至诗。可这份平衡撑了两百多年,到1125年,女真兴起,金朝打上门来,辽朝散了。很多人只记得“辽亡于金”,却忘了辽的余脉没有断。耶律大石,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他带着一批契丹人,往西走。不是转身去争中原,他分明是想另谋一片天。

走西口的不是山西人,是契丹的旧贵族。他们过了沙漠,踩进中亚的绿色洼地,立了一个新朝,叫“西辽”。这里有点像开了个分店:门匾还是“契丹”,顾客却换成了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的人。西辽不去跟中原打个你死我活,而是把眼睛放在商路上,草原做走廊,货物跑两头,慢慢把路修通了——大路通了,词也就跟着跑。
有个市井里的细节挺有意思。中亚人后来把火药叫“契丹雪”,把大黄叫“契丹芦荟”。名字里带着“契丹”,这不是考据癖,这是生活里的顺口溜。一个王朝的名字,变成了药铺里的叫卖,这是词的命,也是人的命。耶律大石的队伍走到那儿,留下的不是只言片语,是带着盐和布的市价,是互通有无的好处。接着,“契丹”这两个字就不再只属于中国北方,它成了“东方”的代号。

讲到这儿,就要把镜头往更西边推。成吉思汗把军旗插在草甸上,马鞍里的地图一摊开,是从中原到黑海的连线。蒙古人有时候干脆,把整个中国的代名词都按“契丹”叫。辽没了?没关系,词还在。金朝占着北方?也还是“契丹”。在他们的脑子里,“契丹”就是东方的那一大片。这个认知,随着三次西征,滚成一团雪,越滚越大。
第三次西征的时候,领军的是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们一路打到东欧,火把照亮了木架教堂的梁柱,也把许多城门烧得发黑。基辅、弗拉基米尔,这些名字后来都摆在了俄罗斯人的心口。有人说那是一个长达两百年的阴影期,是金帐汗国在敲打俄罗斯的脊梁。说阴影也好,说统治也好,毕竟在那段岁月里,语言是会渗透的。学会了缴税,就会学会称呼;学会了递信,就会学会名字。于是“契丹”就从蒙古人的嘴里,跑到了罗斯人的耳朵里。

一个小插曲:1404年,有个西班牙人跑到撒马尔罕看帖木儿——听着像小说,其实是史上有名的使节行程。他在记录里写到,见到来自东方的使节时,口里头就是“Katay”。这不是他自创,他不过是顺着当地的叫法写了下来。你看,词走到这儿,已经不是契丹人的自我介绍了,它变成了别人描述中国的词。
再往里头看看俄罗斯自己的日子。被打痛了不等于不还手。我们总把俄罗斯叫“战斗民族”,那种硬邦邦的劲儿,除了地理的冷与硬,也跟这些年的压迫和反抗有关。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公国们拧成一股劲儿,摩拳擦掌。到1480年,伊凡三世站在历史的节点上,跟金帐汗国彻底分手。蒙古人的统治散了,但“Kitay”这个旧名没散。

为什么?你可以把语言想象成水里的石头,水走了,石头还在。更现实点说,战乱之后,俄罗斯打开窗子,往西望,去学那些觉得漂亮的东西。马可波罗的书就在那个时候翻进了俄罗斯人的书柜。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半生浪迹,在东方见过不少世面。你要是追问他怎么写的“中国”,他大概率会用“契丹”的音。他熟蒙语、懂波斯语,却不说汉话,于是他把“乞塔”掰成了“Kitaia”。书一出来,西欧人纷纷跟着念,从书页到口耳,给东方贴上了“契丹”的签名。
词迁徙的路径就这样清楚了:草原——中亚——西欧,再跳进莫斯科的日常。俄罗斯把它写成“Китай”。音和我们现在听到的一样。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不是。这是文化的惯性,是行走的记忆。一个名称在不同的人口中,被反复使用,就像你家门口的石板路,被数十年鞋底磨出了光。

说到这儿,允许我岔出去一句。莫斯科有个地儿叫“Китай-город”,直译是“中国城”。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系,一直有人争。有人说名字来自“栅栏”的旧词儿,不必拉扯到中国;有人说就是沿着“Китай”的音在脑袋里打的标记。无论哪种版本,听到这个名,我们心里总是会一颤:原来词能走到城市,做一个街区的名。
回头看,“战斗民族”和“契丹”,两个外号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到半路就撞上了。俄罗斯人的硬朗、不服输,是地理和历史合力塑出来的脊背;而我们被叫“契丹”,是另一个时代的遗响。耶律阿保机的旗、耶律大石的路、成吉思汗的马,马可波罗的笔,它们各自忙忙碌碌,最后把一个词推到了今天。

我试着想象耶律大石在西行时的心境。背后是旧朝的余温,前面是陌生的绿洲。他可能没空去想,几百年以后,自己的族名会变成俄罗斯人嘴里的“中国”。他只顾着安顿人,修路,做买卖。词的二次生命是后来人的事。再想想伊凡三世,他拍开了蒙古人的手,却没有把“Kitay”拍掉。有些东西不是敌人的,是时代的,是从四面八方吹过来的风。
当然,也有人会问,“就不能改叫‘China’吗?”语言是习惯的产物。英语里瓷器一枝独秀,连带着“China”成了我们;俄语里更早更广的是“Kitay”,这码事儿一旦沉到民间,就不是谁拍桌子能改得了的。你今天跟莫斯科的大叔聊天,他抬手指一指:“去‘Китай’货店。”你跟他说“我们不是契丹”,他也不懂你在严肃什么。他只是说了一个他从小用到大的词。

我们在意名字,因为名字是识别,也是尊重,更是历史的影子。契丹这个名,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北方王朝,也是一个西去的流亡者的旗帜,后来变成了外人的标签。它比“China”更旧,也更野。你若把耳朵贴近它,能听见马蹄声和风声,能闻到药铺里的大黄味。
所以,当俄罗斯继续叫我们“Kitay”,不必愠怒,也无需矫情。这只是语言里的一段路,走了很久,还没到头。我们常说,时间会把一些东西抹平,也会把一些东西镌刻。契丹这个名,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未来有没有一天,俄罗斯人改口叫“China”,或者我们更愿意他们叫“中国”,也许会,也许不会。名字的命运,往往是人群给的,而不是办公桌上拍出来的。
留个问号吧:当我们把外人叫成“战斗民族”,当他们把我们叫成“契丹”,这些温热的称呼里,装的到底是友谊、误解,还是历史的余温?你走过红场,听到那一声“Китай”,如果心里闪过一阵风,就算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