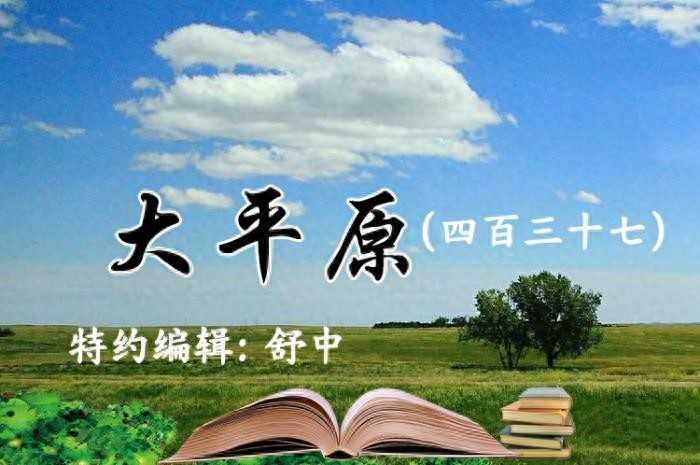
秋天,早市,慢时光
文/王冬良
每天骑车上班都要经过镇上的小市场。起初这里没有早市,只有几个卖早点的摊位和一个固定卖水果的贩子。
只有到了傍晚,或者说下午三四点左右,路两旁才会陆续有售卖各种蔬菜、水果的摊位。他们大多是附近村里的老人,种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园子,把自己家吃不了的笨鸡蛋,丝瓜、茄子、豆角、小白菜、甘蓝、西红柿、黄瓜拿出来换点零钱。
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早上,我突然发现这里除了那几个卖早点的摊位和固定卖水果的,又多了一些卖丝瓜、黄瓜、小葱的老人。后来,人越聚越多,从南到北大约五六十米,路两旁都成了卖水果、蔬菜的人了。有白云湖的藕(当地人叫莲生菜),有章丘大葱,也有小葱;有无花果、葡萄,也有鲜玉米、落花生,有黄瓜、丝瓜,有南瓜,也有冬瓜,有水蜜桃,也有地瓜。渐渐地,一些来自滨州、济阳等临市常年赶集串乡的小商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沾化冬枣、阳信鸭梨、长山山药、东北西瓜、宁夏西瓜等等纷纷亮相登场。他们有说有笑,操着各自的方言,形色各异,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交流着各处得来的新鲜消息,或叹息,或大笑,充满了十足的人间烟火气。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提前从宿舍早走十分钟,打算去小市上买一把小葱。现在卖葱的,大概都会提前一天晚上把菜园浇足了水,第二天清晨去地里拔出来,葱叶碧绿,葱白发亮,根须齐全。我遵照家里老人说的,专买那种不大不小的当葱花用。买回去种在一个泡沫箱里,用土埋起来,随吃随拔,确保新鲜。
卖小葱的摊位有好几个,并不挨着。我看来看去,最终在一位老大娘摊子前停了下来。她卖小葱和大蒜,数量很少,一看就是自己种的,不是那种二倒手的菜贩子。大娘脸上有着不少老年斑,但穿的很干净,人也很精神。我笑着问她,“大娘,您有七十了吧?”她笑了,“八十五了”。她指了指身后的脚蹬三轮,“在家闲着没事,就出来逛游着玩,拿点菜换两个馒头钱。养老钱够花的,我身体好没啥毛病,出来图个开心。”旁边一位大爷看到我买了葱,就问我,“捎着一把豆角吧,天凉了也不长了,都‘落喷’了,再过几天就都拔了,你若想吃露天的就得到明年了。”好在两位老人都备有微信收款码,要不还真的很麻烦。
在公寓做饭的间隙,我时常会安然的坐在厨房门口,抬头看蓝天白云,听隔壁学校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听秋风吹过对面邻居屋顶铁皮的声音,看微风吹动空中的一朵朵丝瓜花和密密麻麻的洋姜叶,暖暖的阳光照在那几棵无花果树上……心里偶尔会有莫名的伤感,孤单。
忽然有一天看到了张炜老师在散文集《我的原野盛宴》中记述大雁“老呆宝”的那段话:“我睡到半夜,常常听到屋外有孤单单的鸟儿在叫,它在连夜赶路,到外乡去。那时我就想,鸟儿和人一样,有时不得不离开大伙儿,自己去一个地方过了。”我又释然了。
心安处,即是吾乡。既然选择了远行,又何惧困难和孤单?换个角度来看,一个人,一间房,一个小院,能够静享这美好的慢时光又是多么难得的事情。这也许是很多人眼中羡慕不来的幸福生活呢!
“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草舍茅屋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如此,甚好。
作者:王冬良,企业员工,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热爱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