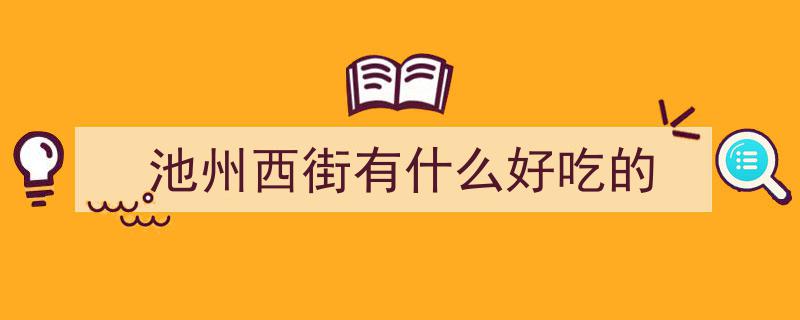阿丁逛池州以平民的视角观赏池州山水 以平常的心态感悟池州文化在安徽池州,有多条商业街被称为“步行街”,但我认为能真正被称为“步行街”的当属杏花村文化商业街,也就是百姓口中的西街——一条没有机动车、电瓶车、自行车的“步行街”,同时,它还是一条文化街、国防教育示范街。




我第一次走过这条街是在1983年盛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池工作,那时,这里是安庆地区贵池县的县治所在——池州地区于1980年初撤销了。芜湖来池的大巴车上,遇见同届毕业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是地地道道的贵池人,家就在当时尚被称为“红旗街”的这条街上,他家的斜对面就是池州镇的办公小院。虽然同届,他却年长我好几岁,是妥妥的兄长。籍贯怀宁的我,在贵池举目无亲,去同学的家就成了我最热切的期盼,而这,也让我度过了初来乍到时的寂寞与孤独,时至今日,我心中仍然觉得,那泡桐树飘落在乱石上的紫色花朵就是世上最艳丽的美,那略显阴暗的平房就是世上最温暖的巢,那高脚杯里盛满的白酒就是世上最醇厚的情,那高低不平的街面就是我人生的坦途......


西街的商业兴起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这里聚集着当时最时尚的新商品、最浪漫的夜生活、最新潮的靓装饰。在百惠兰舞厅,中老年人的国标、年轻人的迪斯科,伴随着或舒缓优雅、或节奏明快的音乐一直持续到午夜;在红蜻蜓鞋店,那一双双款式新颖的皮鞋,尖头、圆头、三接头,黑色、棕色、白色,令人目不暇接;在紫罗兰摄影店,伴随着清脆的快门声,或留下灿烂的笑容,或留下青春的倩影,或留下岁月的印记,在这里,冲印、放大、留存的并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历史,一段人生与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的历史。



西街冠以“杏花村”,且嵌入“文化”二字,是有其因由的。唐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诗人杜牧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并在这里留下了传唱逾千年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因此,以“杏花村文化商业街”命名这条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名称沿用至今的百惠广场中央,有一组以酒为主题的铜雕,
一为村姑担酒,一为村妇市酒,一为村叟小憩,它把《清明》诗中所蕴含的酒文化、诗文化、商贾文化、市井文化隐含其中,可谓是匠心独具。在许多人的心里,总觉得把“文化”与“商业”结合到一起多有牵强。其实,商贾文化从古到今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他们以“诚信”为本,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实现着资本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首创票号以“汇通天下”的晋商是这样,具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商亦如此,更不用说有着“商贾鼻祖”之称的陶朱公范蠡了。

 徜徉在西街,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中,欣喜地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称:百惠、紫罗兰、红蜻蜓、小郭粉丝煲......它们有的或升级或提高,有的仍然经营着几十年前的产品。我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店铺30年经久不衰?是诚信为本?是先义后利?是童叟无欺?是物美价廉?我想,无论是什么,这些都是文化,是商业经营过程中融入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也正是有了这些文化元素的支撑,商业经营才能更加兴旺、更加久远。
徜徉在西街,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中,欣喜地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称:百惠、紫罗兰、红蜻蜓、小郭粉丝煲......它们有的或升级或提高,有的仍然经营着几十年前的产品。我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店铺30年经久不衰?是诚信为本?是先义后利?是童叟无欺?是物美价廉?我想,无论是什么,这些都是文化,是商业经营过程中融入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也正是有了这些文化元素的支撑,商业经营才能更加兴旺、更加久远。


 毗邻杏花村文化商业街,有一条新的商业街,谓“新西街”。新西街名副其实:新的消费群体——年轻人;新的物品来源——天南地北;新的生活方式:欧美韩亚......虽然我很少光顾,但我却能理解并接受,毕竟作为文化,既要有传承,还应当注入新的元素,这样才更能符合时代的特点,文化的传承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毗邻杏花村文化商业街,有一条新的商业街,谓“新西街”。新西街名副其实:新的消费群体——年轻人;新的物品来源——天南地北;新的生活方式:欧美韩亚......虽然我很少光顾,但我却能理解并接受,毕竟作为文化,既要有传承,还应当注入新的元素,这样才更能符合时代的特点,文化的传承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不知不觉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夕阳西下,我留恋地回望西街。街面上,人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抬头仰望,忽然发现,蓝天之下,我心中的西街、笔下的“杏花村文化商业街”竟是“杏村文化商业街”!站在嵌有“文化”二字的商业街街头,我竟是如此没文化,实在惭愧。
不知不觉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夕阳西下,我留恋地回望西街。街面上,人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抬头仰望,忽然发现,蓝天之下,我心中的西街、笔下的“杏花村文化商业街”竟是“杏村文化商业街”!站在嵌有“文化”二字的商业街街头,我竟是如此没文化,实在惭愧。 2023年9月5日初稿 2023年9月9日修改 (文中图片均系作者拍摄)
2023年9月5日初稿 2023年9月9日修改 (文中图片均系作者拍摄)



 我第一次走过这条街是在1983年盛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池工作,那时,这里是安庆地区贵池县的县治所在——池州地区于1980年初撤销了。芜湖来池的大巴车上,遇见同届毕业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是地地道道的贵池人,家就在当时尚被称为“红旗街”的这条街上,他家的斜对面就是池州镇的办公小院。虽然同届,他却年长我好几岁,是妥妥的兄长。籍贯怀宁的我,在贵池举目无亲,去同学的家就成了我最热切的期盼,而这,也让我度过了初来乍到时的寂寞与孤独,时至今日,我心中仍然觉得,那泡桐树飘落在乱石上的紫色花朵就是世上最艳丽的美,那略显阴暗的平房就是世上最温暖的巢,那高脚杯里盛满的白酒就是世上最醇厚的情,那高低不平的街面就是我人生的坦途......
我第一次走过这条街是在1983年盛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池工作,那时,这里是安庆地区贵池县的县治所在——池州地区于1980年初撤销了。芜湖来池的大巴车上,遇见同届毕业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是地地道道的贵池人,家就在当时尚被称为“红旗街”的这条街上,他家的斜对面就是池州镇的办公小院。虽然同届,他却年长我好几岁,是妥妥的兄长。籍贯怀宁的我,在贵池举目无亲,去同学的家就成了我最热切的期盼,而这,也让我度过了初来乍到时的寂寞与孤独,时至今日,我心中仍然觉得,那泡桐树飘落在乱石上的紫色花朵就是世上最艳丽的美,那略显阴暗的平房就是世上最温暖的巢,那高脚杯里盛满的白酒就是世上最醇厚的情,那高低不平的街面就是我人生的坦途......
 西街的商业兴起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这里聚集着当时最时尚的新商品、最浪漫的夜生活、最新潮的靓装饰。在百惠兰舞厅,中老年人的国标、年轻人的迪斯科,伴随着或舒缓优雅、或节奏明快的音乐一直持续到午夜;在红蜻蜓鞋店,那一双双款式新颖的皮鞋,尖头、圆头、三接头,黑色、棕色、白色,令人目不暇接;在紫罗兰摄影店,伴随着清脆的快门声,或留下灿烂的笑容,或留下青春的倩影,或留下岁月的印记,在这里,冲印、放大、留存的并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历史,一段人生与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的历史。
西街的商业兴起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这里聚集着当时最时尚的新商品、最浪漫的夜生活、最新潮的靓装饰。在百惠兰舞厅,中老年人的国标、年轻人的迪斯科,伴随着或舒缓优雅、或节奏明快的音乐一直持续到午夜;在红蜻蜓鞋店,那一双双款式新颖的皮鞋,尖头、圆头、三接头,黑色、棕色、白色,令人目不暇接;在紫罗兰摄影店,伴随着清脆的快门声,或留下灿烂的笑容,或留下青春的倩影,或留下岁月的印记,在这里,冲印、放大、留存的并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历史,一段人生与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的历史。

 西街冠以“杏花村”,且嵌入“文化”二字,是有其因由的。唐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诗人杜牧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并在这里留下了传唱逾千年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因此,以“杏花村文化商业街”命名这条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名称沿用至今的百惠广场中央,有一组以酒为主题的铜雕,一为村姑担酒,一为村妇市酒,一为村叟小憩,它把《清明》诗中所蕴含的酒文化、诗文化、商贾文化、市井文化隐含其中,可谓是匠心独具。在许多人的心里,总觉得把“文化”与“商业”结合到一起多有牵强。其实,商贾文化从古到今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他们以“诚信”为本,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实现着资本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首创票号以“汇通天下”的晋商是这样,具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商亦如此,更不用说有着“商贾鼻祖”之称的陶朱公范蠡了。
西街冠以“杏花村”,且嵌入“文化”二字,是有其因由的。唐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诗人杜牧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并在这里留下了传唱逾千年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因此,以“杏花村文化商业街”命名这条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名称沿用至今的百惠广场中央,有一组以酒为主题的铜雕,一为村姑担酒,一为村妇市酒,一为村叟小憩,它把《清明》诗中所蕴含的酒文化、诗文化、商贾文化、市井文化隐含其中,可谓是匠心独具。在许多人的心里,总觉得把“文化”与“商业”结合到一起多有牵强。其实,商贾文化从古到今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他们以“诚信”为本,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实现着资本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首创票号以“汇通天下”的晋商是这样,具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商亦如此,更不用说有着“商贾鼻祖”之称的陶朱公范蠡了。

 徜徉在西街,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中,欣喜地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称:百惠、紫罗兰、红蜻蜓、小郭粉丝煲......它们有的或升级或提高,有的仍然经营着几十年前的产品。我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店铺30年经久不衰?是诚信为本?是先义后利?是童叟无欺?是物美价廉?我想,无论是什么,这些都是文化,是商业经营过程中融入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也正是有了这些文化元素的支撑,商业经营才能更加兴旺、更加久远。
徜徉在西街,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中,欣喜地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称:百惠、紫罗兰、红蜻蜓、小郭粉丝煲......它们有的或升级或提高,有的仍然经营着几十年前的产品。我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店铺30年经久不衰?是诚信为本?是先义后利?是童叟无欺?是物美价廉?我想,无论是什么,这些都是文化,是商业经营过程中融入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元素,也正是有了这些文化元素的支撑,商业经营才能更加兴旺、更加久远。


 毗邻杏花村文化商业街,有一条新的商业街,谓“新西街”。新西街名副其实:新的消费群体——年轻人;新的物品来源——天南地北;新的生活方式:欧美韩亚......虽然我很少光顾,但我却能理解并接受,毕竟作为文化,既要有传承,还应当注入新的元素,这样才更能符合时代的特点,文化的传承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毗邻杏花村文化商业街,有一条新的商业街,谓“新西街”。新西街名副其实:新的消费群体——年轻人;新的物品来源——天南地北;新的生活方式:欧美韩亚......虽然我很少光顾,但我却能理解并接受,毕竟作为文化,既要有传承,还应当注入新的元素,这样才更能符合时代的特点,文化的传承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不知不觉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夕阳西下,我留恋地回望西街。街面上,人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抬头仰望,忽然发现,蓝天之下,我心中的西街、笔下的“杏花村文化商业街”竟是“杏村文化商业街”!站在嵌有“文化”二字的商业街街头,我竟是如此没文化,实在惭愧。
不知不觉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夕阳西下,我留恋地回望西街。街面上,人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抬头仰望,忽然发现,蓝天之下,我心中的西街、笔下的“杏花村文化商业街”竟是“杏村文化商业街”!站在嵌有“文化”二字的商业街街头,我竟是如此没文化,实在惭愧。 2023年9月5日初稿 2023年9月9日修改 (文中图片均系作者拍摄)
2023年9月5日初稿 2023年9月9日修改 (文中图片均系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