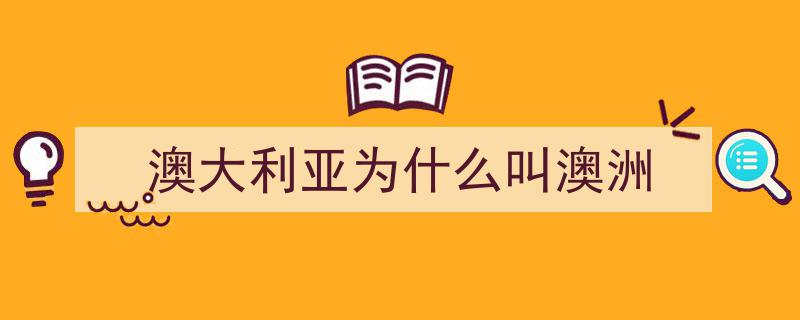由于学习规划,笔者曾被送往澳大利亚的大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学习活动。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头先是涌起一阵激动。毕竟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领略一番外面世界的风采,况且还是公费的,这可是个难得的殊荣。
然而,在喜悦消散之后,沮丧与懊恼便纷至沓来。
由于周围的同学往往将目光聚焦在美国常春藤盟校,亦或是英国剑桥大学、伦敦的高校这类备受全球关注的学府。
相反,对像澳大利亚这类国家的大学没那么看重。
我自己也深受其影响,满心期待着能去欧美游览一番。
然而,自抵达澳大利亚起,这种想法在极短时间里迅速消散了。

人间仙境,“吃货”的天堂
澳大利亚堪称“性价比超高”的人间乐土:全世界最肥的龙虾产自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参也来自澳大利亚,甚至澳大利亚的兔子,都是体型大且肉质肥美的。
澳大利亚的动物既憨态可掬,又行动缓慢,就连其首都堪培拉的金刚鹦鹉,也全无珍稀动物应有的架子,反倒温顺听话。
袋鼠和鸭嘴兽堪称世间绝品,令人喜爱不已。

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动物会显得如此缺乏防护意识呢(说白了就是有点傻)?
1.澳大利亚传统环境以及特殊地理位置
若想探寻这片独特且迷人的土地,就得摒弃传统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在北半球所形成的习惯主义教条。
唯有切实地融入澳大利亚独特的社会环境和别具一格的人文地理,方可切实地解读其中的奥妙。
从3900万年前开始,这片景色宜人的大陆就从南方古陆(亦称“刚瓦伦古大陆”)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区域。

从那时起,它就踏上了独立发展的征程,这也是如今它的物种极具独特个性,和亚欧大陆物种存在差异的关键缘由。
因为地表运动极为“迟缓”,而风化侵蚀作用却十分“勤勉”,所以留在澳大利亚地表的营养层(亦称“腐殖质植被”)愈发浅薄,由此当地孕育的植物通常只能获得较少的养分。
在这般“糟糕”的环境之中,澳大利亚的其他树种相继灭绝,仅有一种高大的乔木——桉树,依旧艰难地“独自坚守”。

屋漏偏逢连夜雨
由于澳大利亚所处纬度较低,使得蒸发量极大,再加上降水毫无规律,这让澳大利亚的树木不得不开启进化进程:树叶愈发变小(目的是减少水分蒸发,维持水分平衡),植物液体也变得富含更多油脂(既保存营养物质,又能保护自身)。
与此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由于桉树树叶不但营养成分少得可怜,还难以下咽(稍不留意就会扎到嘴巴),使得众多素食动物因食物匮乏而死亡,存活下来的动物只能迫使自身进化出能够咀嚼桉树树叶的口器以及可以消化它的胃。
萌态十足的考拉堪称这之中的杰出代表。

即便如此,在全球现存的650多种桉树中,可供考拉食用的桉树种类不足50种。
2.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时代的要求促使着进化,而丛林法则也必然推动这一趋势。
在这极为糟糕的环境面前,为了存活下去,澳大利亚的动物们只好选择勇敢面对挑战。
它们不但得承受食物味道不佳之苦,还需时刻提防面临“没东西吃”的风险。
大脑作为高耗能的首要器官,自然最先被它们舍弃。

以人类来说,大脑的能量消耗极为惊人,仅占人体重量4%的大脑,却会消耗掉人体25%的能量。
这是人类在残酷自然面前所做出的抉择,在当下的我们眼中,这个抉择无疑既正确又伟大。
但澳大利亚以考拉为首的哺乳动物可不这么认为。
于是,考拉逐渐演化(注意,并非退化)成了地球上现有的脑容量和体重比例最小的哺乳动物。
尽管它的脑袋看上去挺大,然而其脑部大小仅和一颗核桃差不多。除此之外,考拉每日的睡眠时间竟超过二十个小时。

鉴于它慵懒的习性,其活动范围极为有限,一生仅仅占据几棵树的空间。它堪称动物界秉持“活着只为吃饭”观念的头号动物。
了解事情真相的笔者目瞪口呆。
此外,并非只有考拉如此,澳大利亚差不多所有动物都选择了“绿色节能生活”,它们把自身的脑容量变得极为微小,每日除了进食便是睡觉。
更为偏激的情形下,有些动物养成了饱餐一顿后便十天半月都不活动的极端习性,像澳大利亚广为人知的两大顶级捕食者——鳄鱼和毒蛇就是如此。

3.独立进化,自成一体
由于澳大利亚在3900年前就从古大陆分离出来,宣告“独立”。
故而如今澳大利亚的“本土生物”均是独自进化形成的。毕竟它们大多头脑愚笨、行动迟缓,彼此间基本能和平共处。
甚至澳大利亚近乎唯一能够快速行动的本土生物种类:袋鼠。
同样是抉择将自身有限的养分输送给“健壮体魄”,而非“聪慧头脑”。

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地理状况,使得当地物种能够独立进化,无法和外界开展物种交流。就这样,憨厚的澳大利亚本土生物逐渐演化得更为“萌态可掬”。
当下,让澳大利亚政府最为苦恼的事情既不是“推动经济发展”,也不是“健全民主制度”,而是物种入侵现象。
全球化——潘多拉的魔盒
地理大发现之后,澳大利亚彻底进入了世人的视野。
与之相对的是,不同的物种也被殖民者们带进了这个“遗世独立”的土地上。
由于自身不存在天敌,并且具备极为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它们于澳大利亚各处繁衍开来。
排在最前面的当属由“亚洲锦鲤”领衔的亚洲淡水鱼群体。
澳大利亚政府眼下最为头疼的难题,是亚洲淡水鱼在当地疯狂繁衍,其数量之多甚至造成了河道堵塞。

他们每年都会耗费大量资金,派遣专门人员打捞,随后直接实施“土葬”。
由于他们嫌淡水鱼“腥味过大”且“刺太多”,故而大多不想吃。
为了守护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笔者抵达此地后,时常会在闲暇时去钓鱼(别误解,澳大利亚不像德国那样有诸多限制,在澳大利亚,钓鱼属于公益活动,不少学校还专门设置了钓鱼喂鸟的区域)。

而且把那些被澳大利亚人当作“洪水猛兽”的亚洲淡水鱼吃得有滋有味。
请不要问我吃了多少次,反正笔者回国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再吃鱼了。

今日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关注我,获取更多信息。
诚挚各位在屏幕下方留下您的珍贵见解。
废青工作室与您下期不见不散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收集,若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文:小昭
审核:梦愚编辑
文献引用:《史记》《战国策》《二十四史》《汉书》《后汉书》《诺贝尔奖》《二战全史》《二战通史》等
本文为一点儿历史事作者手打,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