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地名的语言交融探析,东南亚语言接触现象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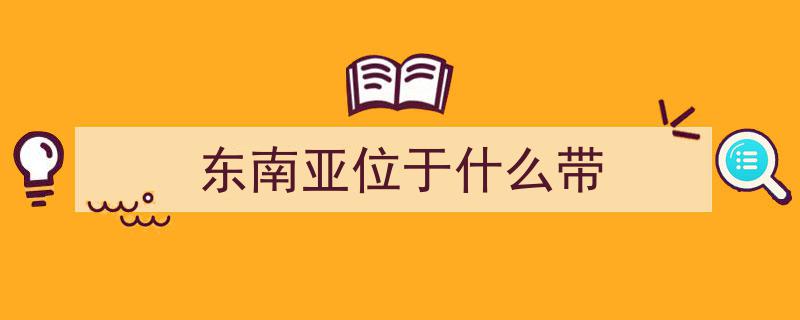
我们来探讨一下越南与东南亚的语言接触,并以部分越南地名为例。
越南地处东南亚,其语言(越南语)与该地区多种语言,特别是与占语(Austroasiatic语系)以及其他南方语言(如壮侗语系)以及后来接触的汉语(Sinitic语系)和泰语(Tai-Kadai语系)等,都存在长期的、复杂的历史接触关系。这种语言接触深刻地影响了越南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并直观地反映在其地名上。
"越南与东南亚语言接触的背景:"
1. "古代居民的迁徙与融合:" 越南主体民族京族(Kinh)的祖先被认为是古代百越族群的一支。百越族群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大陆,包括中南半岛。他们在迁徙、扩张和与其他族群(包括占人、老挝人、泰国人等)的接触、融合过程中,其语言与其他语言发生了持续的接触和相互影响。
2. "地理邻近与文化交流:" 越南与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山水相连,历史上长期的贸易、通婚、战争以及文化交流,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和借用。
3. "汉语的影响:" 自汉唐以来,越南长期处于中国的影响之下,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文化载体和书写系统,对越南语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词汇(尤其是政治、文化、科技词汇
相关内容: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关注
摘要:研究东南亚的学者都承认接触交流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接触过程不仅具有持久性,而且在源头上具有复杂性,由此形成了持久广泛的影响,并使民族文化画卷更加绚丽多彩。在此过程中,语言接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越南地名的研究能够更加清楚这种语言接触的结果,进而丰富东南亚地区广泛文化交流的例证。
关键词:语言接触;越南;东南亚;地名
0
东南亚的文化空间
东南亚是亚洲的一个次区域。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这是世界历史上首先出现人类的地区之一。同时,这里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农业地区之一。换而言之,东南亚的文化空间具有显著的稻作文化特征。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东南亚亦被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其与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最早。而且在文化接触过程发生之前,东南亚的本地特色文化已有所发展。研究者认为,东南亚的文化接触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纵横交织、多维多向,是一个既发散又汇聚的过程。东南亚的文化接触交流有助于丰富当地文化,因此,该区域的文化图景呈现可谓“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已故越南著名东南亚研究专家Phạm Đức Dương教授(2007:12)曾说:东南亚的文化画面如此多样化,以至于“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实是怎样的”。因此,文化接触是东南亚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有助于全面了解该地区的文化历史。
东南亚文化空间中的语言接触必不可少。广义上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接触,因此,可以将语言接触视为文化接触的一个方面,而语言交错是文化接触和传播中的一个方面(Nguyễn Văn Khang,2007)。事实上,由于语言来源或语言接触的关系,东南亚文化中有许多相似语言特征的族群,这些族群或相邻而居或相距甚远。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各族群间出现迁徙和混居,语言接触也就成为必然。因此,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及文化接触展现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1
东南亚背景下的越南语言接触
尽管仍有许多不同意见,但现在越南大多数研究人员一致认为东南亚文化中的语言可以划分为5个语系,分别是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壮侗语系、苗瑶语系和汉藏语系(Trần Trí Dõi,2015)。其中,南亚语系的使用者最多,几乎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也被认为是东南亚地区最古老和最本土的语系。
越南位于东南亚大陆与东南亚岛屿的交界处,历史上许多移民在此交汇,因此成为了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地区,通常被称为“微型东南亚”。越南的语言可以分为5组,分别对应东南亚的5个语系。越南语是越南的国家语言,也是越南人数最多的民族—京族的语言,被归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越—芒语支。该语言分支是南亚语系中最重要的分支。识别语言的起源通常很复杂,而确定越南语的起源就更为复杂(Trần Trí Dõi,2011)。因此,关于越南语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研究结果。越南语曾经被归类为壮侗语系,甚至是汉藏语系或南岛语系。如上所述,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接触导致了很多变化,其中包括语言的变化。因此,越南语除了保留相当部分的原始语言基本词汇外,还在早期的语言接触过程中借用了很多外来词。正是这些语言接触,导致很多研究人员错误地认为越南语属于壮侗语系、汉藏语系或南岛语系。事实上,越南语和壮侗语系、汉藏语系或南岛语系的相似性是几千年前语言持续接触的结果。
为阐明语言接触的过程,本文拟从越南与东南亚的语言接触来看越南的地名。
2
越南地名词源的多样性
可以肯定的是,地名是越南文化多样性在语言方面的重要体现,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地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该变化可以是语言的纯粹转变,通常是语音的转变。例如,瑞雷村(河内市东英县瑞林乡)亦有喃字名称其为(Nhội)村。Trương Nhật Vinh(2015)指出,(Nhội)是语音转变的结果,喃字名称中的第一个辅音nh/ɲ/是辅音ml/mnh变化的结果。之后,该村名汉越化成魔雷,但由于魔字在越南语中有不好的意味,所以改成春雷,随后继续变化,更名为瑞雷。
地名的多样性还反映在历史上语言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红河的名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红河的每个名字都被视为不同阶段语言接触的印记。Trần Trí Dõi(2011)指出,红河作为越南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条河流,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如滔、蕊/耳河、富良、百鹤、三带、大皇、赤藤、皇江、泸/泸江,其中,富良、泸/泸江被认为是其早期的名字。此外,人们还称红河为大河。法国人到达越南后,观察到由于淤泥的原因使得该河河水呈红色,因此称其为“红色/红棕色的河”(rivière rouge),红河这一称呼出现于19世纪。在这些名字中,只有泸江和富良江来源于纯粹的越—芒语支,而滔的称呼源自泰语,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越词名称。一条河流在不同阶段的名称变化,体现了越南不同时期的语言接触。
越南源自南岛语系的地名并不少见。例如,通过对西原地区多乐省和多农省的实地考察发现,1513个显示自然地理特征的地名中,有725个地名(占48%)属于埃地族语言名称(Nguyễn Minh Hoạt,2013)。然而,河内及河内周边区域的南岛语系地名并没有这么高的比率。虽然其数量不多,但河流的名称变化可以反映出非常重要的问题。Trần Trí Dõi(2001)已经证实并指出:河内郊区那些源自南岛语系的地名,如嘎箩河、浣溪乡、褚赦乡的圣乾海、古螺等,可以证明几千年前南岛语言的使用者曾经居住在该地区。目前,在越南的中南部、西原和南部地区仍有很多地名源自南岛语系,因为这些地区曾经或现在是南岛语系使用者的栖息地。南岛语系地名出现在北部平原地区,即越南文化的摇篮具有特殊的意义,说明在越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长期存在着文化融合,其与南岛语系居民的接触被视为越南语言文化史上最早的接触。
越南语与岱—泰语的接触也在越南的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越南语语音学研究显示,历史上越南语在南岛语系之后接触到壮侗语系,也就是说,这种接触“在越南的东山文化时期尚未发生”(Trần Trí Dõi,2017)。正因为这种接触发生较晚,源自岱—泰语(壮侗语系)的地名比源自南岛语系的地名更多,也更容易识别和确定。越南文化学、民族学及语言学领域的Trần Quốc Vượng,Phạm Đức Dương,Hoàng Lương等著名学者均认为带有Dền-Chiền-Triền-Viềng、Na/Nà、Noi等元素的地名源自岱—泰语。
当今越南的地名研究者早已清楚认识到地名起源的多样性,因此他们以语源为标准对地名进行了分类。例如,Lê Trung Hoa(2018)将越南地名分为4组,即纯越地名、汉越地名、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和外语地名。Nguyễn Văn Âu(2008)则将越南地名分为3个区域:南亚地名区域、南岛地名区域和汉藏地名区域,又继续细分为8区和15区,如南亚地名区域指几乎北部所有地区、整个中北部地区、西原大部分地区、南中部大部分地区及南部所有地区。根据这种分类,南部属于南亚地名区域,因为除了纯越地名外,还有高棉语(南亚语系的一种语言)地名。这两位学者的分类都从共时角度准确反映了地名的情况,然而从历时角度来看其“纯越”性,还需要仔细考虑历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因为此种分区方式忽略了很多特例,而这些特例正是语言接触中最深的“印记”。例如,在理解承天—顺化省豉乡中的“豉”,该语音来源自占婆。豉乡的喃字名称是赖恩,现在属于富荣县富茂乡,距顺化市约8公里。总的来说,承天—顺化省属于北中部,在此生活的主人是占婆国(大越国南部地区一个文化繁荣的古王国,该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属于大越南部,尤其是1306年玄珍公主嫁给占城王制旻后)的占族人。因此,在理解该地名时,有必要考虑这个地方的历史形成、发展背景及不同族群居民在此的接触交流情况。笔者要证明的论点是:sình/ʂiɲ2/的音节首辅音与/ciɲ2/中的舌面音擦音现象有关。在占婆语中,有一种ching/ciɲ/或/ciŋ/的语音形式,其意义是“刻、划、截(成图章)”。因此,该地名是以乡里的“版刻”版画艺术来命名的;占婆语中的ching音越化成了如今的Sình音。因此,赖恩乡的喃字名是豉乡,因为该乡有“版刻”版画艺术。该地名是历史上越—占语言文化交流的结果。
Phạm Đức Dương曾写道:“······通过对地名的研究,我们将了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部分历史,知道其主体来源与我们正在研究的其他主体地名的联系接触,或多或少地了解族群在时空中的演化过程。”(Phạm Đức Dương,Phạm Văn Lam,2013:61)。虽然没有强调语言接触,但是其重要性肯定有助于我们强化这一观点,即在越南的地名研究中,语言接触尤其是历史上的语言接触,是完善越南地名知识及越南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3
汉越地名与越南地名汉越化方式研究
3.1 越南与东南亚及中国的语言文化接触
Phạm Đức Dương(2007)认为,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密切,主要有以下4个特征:首先,中华文明对史前东南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南方农业稻作文明的重要要素;其次,中国有一部分海外华侨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位尤为重要;第三,中国有部分岛屿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后,在传统国际关系中,中国有两条通往世界的贸易通道,其中包括通往东南亚大陆与岛屿国家居民居住区的海上道路。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接触非常早,始于秦末。越南文化中浓重的中国印记始于汉代,因此中国与越南的语言、文化接触往往被称为汉越接触。除了两国地理、政治、历史、经济之间的影响因素之外,越南语与汉语的接触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两种语言是同类型的独立语言(有音调、音节,用词序来表达语法关系等)。越南语借用了汉语中许多元素,如借汉词和汉源成语,汉字也为汉越间的接触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每个阶段的汉字功能都不一样。因此,汉越接触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研究汉越接触时,研究者主要关注词汇方面。地名作为词汇的一部分,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地名作为汉越接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越南学研究领域里,也有中国研究人员认识到地名这一有趣的研究对象,他们从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学等不同角度来探讨。《越南语文化语言学》(祁广谋,2006)和《越南语言文化探究》(范宏贵,2008)两本专著中均有提及地名,并认为“地名是研究越南语言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对象”(陈继华,2011)。
3.2 汉越地名与地名汉越化的方式
越南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接触始于公元伊始,但那时用汉字记录地名只是统治者的事。在此期间,行政区划和行政单位不具系统性与规模性。因此,如果有汉越地名,则主要是政府管理的行政单位或以河流、主要山脉等典型自然地理单位命名。那时表示规模较小的居住单位地名或小型自然单位地名如村、堡、乡、丘、溪、潭、湖等主要是用喃字命名。自越南独立时期开始,汉语和汉越读音成为越南的行政语言和语言文学,因为各朝代为了方便管理,需要记录和管理地名,喃字地名逐渐被汉越化。阮朝时,嘉隆王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地簿,之后明命王进行了行政改革,越南的乡村地名系统基本被汉越化。
因此,汉越地名在越南地名中的数量很多。然而,由于许多原因,地名的数量和汉越化在各个地区的公布不均。在北部和北中部地区,乡村地名中出现了喃字地名与汉越地名并存的现象。北部平原地区有96.2%的喃字地名附有汉越名称,海防虽然也是北方的一个省,但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的特点,只有约70%的汉越地名(Nguyễn Kiên Trường,2005:50)。在中北部,该比例有所下降。Nguyễn Văn Loan(2012)表示,河静省30%的地名有汉越元素。据Từ Thu Mai(2004:46-47)的《关于广治地名的研究》,该地只有约30%的地名有汉越元素,其中以汉越元素与纯越元素相结合而创造的地名约占6%。与北部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广治几乎没有喃字地名与汉越地名并行的案例,因为广治以前是占族人的土地。汉越地名的比率在其余地区继续下降。在西北地区,汉越地名的比率仅占不到15%。例如,在太原省武崖县的考察发现,只有近13%的地名有汉越元素,而且这些汉越元素的地名主要是后来的行政机构按照居民单位命名所得(Trần Văn Sáng,2013)。
行政地名在汉越地名中占有很高的比率。阮朝时期,河内—升龙城82.19%的行政地名有汉越元素(Nguyễn Thị Việt Thanh,2015)。现在越南南部有2373个行政地名,只有509个地名不是汉越名(Lê Trung Hoa,2010),因为汉越化的首要目的在于行政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越南人的意识里,喃字名称往往是村野的、平实的、淳朴的,并自发地认为汉越名称常有博学、典雅、庄重等寓意,饱含了人们对安、顺、大、义、平、福、泰、和、美等美好愿望的渴求。因此,之后用汉越新名替换喃字旧名的趋势使得行政地名的汉越化更加明显。
显然,汉越地名是汉越接触的结果,其中既包括语言接触,也包括文化接触。因此在阐述通过语言接触来进行地名研究时,将汉越地名单独列举有特殊用意。首先,在研究借汉词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虽然许多研究者认为“gần(近)”源自汉语词根“近(JÌN/CẬN)”,但Trần Trí Dõi(2016)认为,从前越—芒语时期到现代越南语的语音历史变化表明,越南语中的“gần(近)”这一单词并不是汉越化现象的结果,而是源自南亚语系纯粹的越南语。汉越地名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史料中对许多汉越地名的来历都有明确记载,以此为依据就很容易判断其是否有汉越接触。然而,并非所有的记录都可以成为研究者进行分析的基础。例如,近期一篇关于河内东鄂乡地名研究的文章提到,东鄂村的喃字地名是“ ”,其对应的汉越地名为东鄂乡。根据汉喃资料显示,其记录为“東鄂”与汉越地名一致。基于汉字,可以查到地名中每个元素的含义。然而,当结合两个元素的含义时,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也无从知道这两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此外,其喃字地名和汉越地名之间没有反映出任何语音规律或者联系。地名尤其是汉越地名,必须被视为文化、历史转型过程的见证。这将是一片等待越南学研究者继续开发的土地。
4
结论
地名是对某一地方的称呼,是区分不同地方的地理空间,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短语。用于命名地点的词或短语可以反映其特征、出现时间以及人们的认知。此外,社会因素的变化或语言本身的转变也可能导致地名变化。地名研究有助于理解与历史、文化、语言相关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地名还是语言和文化接触过程的证据。从语言和文化接触的角度研究地名,有助于研究者对东南亚文化空间中的越南有更广泛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陈氏红幸 朱斯
来源:《当代外语教育》2020年第0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宋柄燃
校对:王玉凤
审订:江 桐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