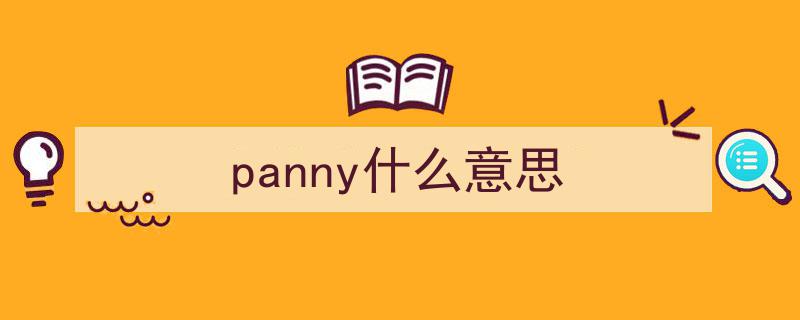2024+2025双年、2025+电子刊,组合下单更优惠 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 王汉洋
【导读】美国众多前工业城市曾经创造一个个改变历史的辉煌成果,从水泥、钢铁到橡胶,这些城市和它们的人们为人类的工业文明打下了最初的模板。然而在全球化夺走他们的订单、一座座雄伟的工厂关闭之后,当地社会陷入无望的停滞与层出不穷的犯罪之中。直到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才让全世界看到这群长久被遗忘的人们。这些失意的选民用自己的选票和捐款把一个承诺代表他们利益的富豪选成总统,开启了美国新一波保守主义的浪潮。如今,特朗普又一次当选。然而在一次次贸易保护主义和振兴制造业的政策之下,老工业区的经济却并没有真正改变。本文指出,只要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整体目标不变,制造业就必然处于重重死结之中,难以回归。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不过是喊给这些人的无法兑现空洞口号而已。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原题为《美国新梦:只跟社交网络有关的制造业回流》,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快九十岁的宾州老人 Ed Pany 总是和来访者从 1950 年代初开始讲起:精神失常的日本见习僧人烧毁了金阁寺、艾森豪威尔以国防名义建立连接全美的高速公路网络、苏联则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大幕。不过外部世界纷纷扰扰都与正在上中学的 Ed 没有关系。
Ed 只关心他能不能多干点、再多干点、多给一些水泥口袋封口。Ed 贫穷的父亲从即将解体的奥匈帝国来到了美国,落地在宾夕法尼亚州北安普顿。到 Ed 出生时,家里情况开始逐渐稳定,不过依然需要每个人都尽早工作。
正准备上中学的 Ed 并不讨厌工作,相反他迫不及待。伴随着二战结束,美国蒸蒸日上的经济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机会。Ed 来到了家边的水泥厂,负责把铁丝套在麻袋然后用机器把铁丝缠绕上去封口。一套、一钩、一拉,几分钱就到手了。

手捧水泥袋的 Ed
Ed 就这样一直干到了 16 岁上大学,他依靠自己用缠水泥袋子挣的钱,付了学费。一个人,靠水泥袋子挣出了自己的学费,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Ed 也知道这点,所以他才会在博物馆里,给所有访客讲述这个过去的故事。一个比房子、车和狗更令人激动的美国梦。
这个博物馆几乎是靠 Ed 和他女儿 Panny 两个人建立起来,展厅不大,主题只有一个:阿特拉斯水泥厂的历史。
阿特拉斯水泥厂和博物馆一样,坐落在北安普顿。当地人曾自豪地称这里为「世界水泥的首都」——它确实有资格。阿特拉斯水泥厂发明了批量生产波特兰水泥的方法。今天没人再提「波特兰水泥」这个名字,因为现代社会使用的所有水泥都属于波特兰水泥。
光有技术还不够。北安普顿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李海河谷(Lehigh Velly)。这条河谷在大阿帕拉契山谷中,长 64 公里,宽 32 公里。丘陵峡谷的地貌让人们很容易取得这里的石材,一种由不太纯的碳酸钙构成的深灰色石头。其中包含的铝、铁等成分可以大大增加水泥的强度,以至于人们直接将其称之为「水泥石」。优质的原料结合阿特拉斯的技术,千座山峰化水泥。
李海河谷是美国工业化的起点。在前电力时代,河谷湍急的水流能提供最好的动能。河谷最开始只是一群摩拉维亚人的定居点。摩拉维亚人因为反对天主教会,不得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流窜于欧洲各地。也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点可以傍身的手艺。来到新大陆后,他们用圣经中的名字来命名河谷两岸的地点,其中最主要的一处叫伯利恒。早在美国建国之前,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摩拉维亚人就在伯利恒干起了皮革作坊、磨坊、铁匠铺……

李海河谷的列车
之后,随着美国正式建立、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伯利恒始终位于美国工业之路的延长线上。最终这里诞生出了一个璀璨果实:伯利恒钢铁厂。伯利恒钢铁厂发明了工字梁,今天全世界所有摩天大楼里,都在使用这种钢材。伯利恒钢铁厂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在二战期间,它开足马力为美国建造了 19 个不同级别的 1127 艘战舰。它的雇员开玩笑说:「没人能在钢铁厂想小事儿。」
工业的发动机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料。而在水力之后,里海河谷的巨型矿脉又为美国工业贡献了大量无烟煤。有许多类似 Ed 父亲的外国移民作为劳动力、还有充足原材料、先进技术和批量生产,这简直就是工业化天堂。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片被上帝眷顾的土地光是有这些还不够。另一份礼物,是一块巨大的、不论建多少高楼都几乎不会沉降的花岗岩。
这块花岗岩,叫做纽约。
阿特拉斯的水泥浇筑了通往纽约的海底隧道,又和伯利恒的钢铁一起建造了帝国大厦、洛克菲勒大厦 ...... 一座座摩天大楼在纽约升空,这是美国工业化成果的应许之地。
光是建造美国还不够。阿特拉斯水泥厂从北安普顿群山中开采出来的石头,又来到了南北美洲之间的遥远热带。北方森林的一座山,变成了南方的一条河。这条河就是巴拿马运河。在一百多年前水泥还是高科技时,人们跨越一个大洲去运送它。不光跨过大洲,还要跨越大洋。日本大量从阿特拉斯采购水泥,直到用这些水泥建造的设施造出了武器,偷袭了珍珠港。当年阿特拉斯水泥厂可以出口全球,今天鹤岗的水泥因为运费甚至卖不到佳木斯。
这是美国工业化的辉煌年代,一场黄金色的大梦。
梦消失有时是渐渐的。
二战后,水泥逐渐在各国普及。面对全球化竞争,阿特拉斯水泥厂只好逐步减产。得益于水泥厂研究室发明了白水泥,阿特拉斯又得以继续坚持了一段。直到 1982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2:37,厂长办公室的呼叫系统中传来了这样一句话「现在请听我说:1 号烧窑已由 1 号烧窑工罗伊-威尔正式关闭。我们现在将为垂死的工厂奏哀乐。」北安普敦工厂 1 号白窑熄火,那个建造现代世界、跨越大洲去建造运河的故事结束,太阳在世界水泥之都落山。
几十年之后,留下来一个祥和的小镇、两位老人与博物馆、几个被当作露营地的巨大矿坑、和一堆倒掉或快要倒掉的窑炉。只有少数在意它的人还在为它乞讨。如果不是当地文保机构呼吁大家捐款保护这些即将消失的工业废墟,都没有人会意识到散落在小镇各处的遗迹意味着什么。
更多梦是轰然坍塌,留下了一地鸡毛。
2024 年 6 月,几个中国访客正在巴尔的摩的内城区一路向前开。目的地是费耶特街与门罗街的街角。可他们越往前开越感觉不对劲。工作日的下午两点,路两旁半废弃的排屋前站着一些成年和未成年男性。门罗街的前一个街区,短短几百米的路上站了十二个无所事事又三两成群的人,每个人都在盯着这台车看。最不会读空气的人也能意识到:所有人都认为这台车、和车里的人不属于这里。要么赶快离开,要么就指不定发生什么了。
最后这台车里的访客连在车里拍照都不敢,看了一眼费耶特街与门罗街的街角就加速溜走了。而把他们吓跑的原因恰恰是吸引他们来的理由。因为这里是名为《街角》(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urhood)一书故事的发生地。前记者大卫·西蒙用了一年时间,记录下了一群边缘人在这个街角关于毒品、犯罪、希望和无法得到救赎的故事。后来,西蒙依靠包括《街角》在内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部经典美剧《火线》(The Wire)。
《街角》出版的 1993 年,巴尔的摩发生了 353 起凶杀案,每十万人 48.2 起。三十年后的 2023 年,发生了 262起凶杀案。看起来确实有所减少——但介于巴尔的摩人口的持续下降,每十万人里依然还有 46 起。如果放在上海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年发生 11389 起凶杀案。加速离开的中国访客,确实有理由担心自己别成为明年数字的一部分。
是什么造成了巴尔的摩的一切呢?最开始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之后是一个哭不出来的笑话。
也许是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这里有了工业;也有可能是反过来,某地有了工业,接着聚集了一群人。随着国家发展,产业壮大、人口增加,就有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后来成本竞赛升级,产业逐渐向更便宜的地方转移;可大部分人并不会跟着走,他们只能留在原地。这些城市皆依赖工业崛起,所以工厂往往在最核心的内城区。工厂搬走或关闭后,城市就先有了一个黑点。接下来生活开始迅速被这个黑洞一样的点影响,逐渐整个内城区都变成了一个破洞。街角就在这样的破洞里。
在美国,有一个特定形容词来说街角这样的地方:Hood。Hood 就是无数巴尔的摩街角组成的破洞,它出现在了所有曾经工业化的美国城市里。这些城市的破洞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国家的窟窿。
那个帮助美国打赢了二战的伯利恒钢铁厂倒塌了,连带着让位于巴尔的摩的伯利恒造船厂也一起垮了。十几万工人突然失去工作,也让所有依靠他们活着的人都没了饭碗。造船厂还顺带弄没了退休员工的养老金。

巴尔的摩的断桥,因缺乏资金而无力修复
巴尔的摩迅速塌陷,生活也跟着沦落了下去。没用工作、没有钱、没有饭吃,更重要的是没人需要他们了。昨天还引以为傲的技能,今天变成了需要遗忘的绊脚石。无数人始终忘不了自己的昨天,他们也就没能走到明天。酗酒、吸毒、暴力 ...... 一个人沾上这些问题是命运的悲剧,可如果一群人都是碰到这些事儿,那就是社会的苦难。所以巴尔的摩的街角才如此危险。
美国不只有一个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好歹还是个戏剧性的大城市,绝大多数失去工业的地方,连凶杀案都没力气发生。
更多窟窿不会变成巴尔的摩,会变成那些开了一辈子高速都不会下去看一眼的地方。
合众国第 50 任副总统 J·D·万斯的老家米德尔敦就是这样的窟窿,此地目前一无是处。米德尔敦是「Middletown」的音译,名字源自地理位置:处在莱特兄弟起飞的代顿和辛辛那提中间。这名字起的都足够证明这里乏善可陈。
米德尔敦最开始只是依靠农业和造纸厂,但当 1900 年美国轧钢公司(ARMCO)在此开设薄板钢轧制工厂时,它成了远近闻名的钢铁城镇。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全美钢铁公司利润的下降,米德尔敦也逐渐生锈。
想像一个最无聊的城市:没有主要产业、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名胜古迹、酒吧也开不下去,甚至连涂鸦都没有多少。墙上有生殖器的涂鸦好歹证明一个地方还有人想搞点乐子,可惜米德尔敦连这都不拥有。沃尔玛里中国生产、号召大家 2024 年大选投票的 T 恤清仓只要一块。甚至都没有任何人对这里出了一位副总统有任何的感觉,整个城市对此事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唯一的乐子是万斯旧居的隔壁邻居支持哈里斯。
再想象把米德尔敦复制粘贴一百个,然后换上不同的名字。比如坎伯兰、惠灵、扬斯敦、尤宁敦……尤宁敦可能稍微好点,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这里发明。该怎么理解这些工业消失之后,被称之为锈带的地方呢?那些老生常谈的论述把这群地方描写成破败、悲惨、挣扎的样子。可能都没错,但这些地方最大的特点是无聊。因为它们已经一无是处了,是没人需要的地方和没人需要的人。不被人需要,能有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悬崖边的小石块,努力不被风吹下去但已经快挺不住了。
梦醒之后的美国。经济依然增长,但一群人就这么被落下了。他们已经被忽视很久,终于有人注意到了他们。2016 年,一个局外人振臂一呼;众人才纷纷注意到:原来那些高速公路旁边路过了一辈子的窟窿,是有人住的。
超级大国里的一群失意者,希望对抗二战以来全球化自由贸易的趋势,把自己的工作、把制造业、把那些让自己祖辈自豪的事物夺回来。特朗普、拜登、和特朗普接下来的任期里,美国的政治家们纷纷许诺,美好的日子将会回来,美国将会重新伟大。美国,将会有一个新梦!

长满植物的废弃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工厂
「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口号非常有迷惑性:带回制造业本身就是困难目标,但在这里它变成了让美国伟大的手段。目的变成了手段、结果被说成方法。从而避开了真正的问题:工业化很难,再工业化同样难,具体该怎么办?
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可以加大对制造业人才的培养,吸引投资然后通过关税等各种手段将企业拉过来,就可以逆转去工业化的趋势。这种视角把去工业化看作是一个循环性周期,而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就像是天气循环一样。可去工业化不是天气现象。相比去工业化,现实里城市在自然灾害前往往更有韧性。
去工业化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是很难用过往方法去解决的,因为结构性就意味着大部分曾经有效的方法都失效了。
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就是个微观例子。阿克伦是典型锈带城市,当年却是整个美国工业化故事起源之一。在这里兴建的俄亥俄运河将五大湖和哈德逊河连接起来,在十九世纪初促成了俄亥俄州和宾州两个工业大州的兴盛。可以说是那些我们熟知美国黄金时代工业奇观的长辈。后来阿克伦抓住了橡胶工业。1898 固特异成立于此。和水泥之都类似,这里被称作世界橡胶工业之都。
就像其他的那些去工业化城市一样,阿克伦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经历了剧烈衰退。运河早已不再是工业必需品,甚至运河旁干净明亮的洗手间里都没有水。全球化浪潮把阿克伦的橡胶工业拍在了岸上,它失去了接近两万个工作岗位。日本、德国接过了阿克伦手中的橡胶,让它成为了典型全球化失败者。
为了挽救自己,阿克伦做了什么呢?
首先,阿克伦在大方向上没问题。固特异这样的大公司没有完全撤出阿克伦,并且市政府还通过各种加速器吸引新企业。有超过 400 家聚合物相关公司在这里运营。聚合物几乎可见在现代生活每个领域:电脑、杂物袋、纺织纤维和海水淡化膜都要用到聚合物。市政府努力让亚马逊把巨大的物流中心放在这。除此之外,还有一万五千名年轻学生就读于本地的阿克伦大学。
科技公司也喜欢阿克伦遗留的基础设施。Google 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创办的神秘飞艇公司 LTA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于 2023 年在阿克伦租下了曾属于固特异飞艇的巨大机库。这座「茧」型机库堪称美国工业化黄金年代顶点的象征:面积大于八个足球场,拱形大跨度完全没有柱子。每扇大门重 600 吨,门下每个轮子都要由一个独立的发电机。启动时,需要 5 分钟才能把门打开。甚至因为建筑过大、过于空旷,湿度高的时候室内会下雨。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