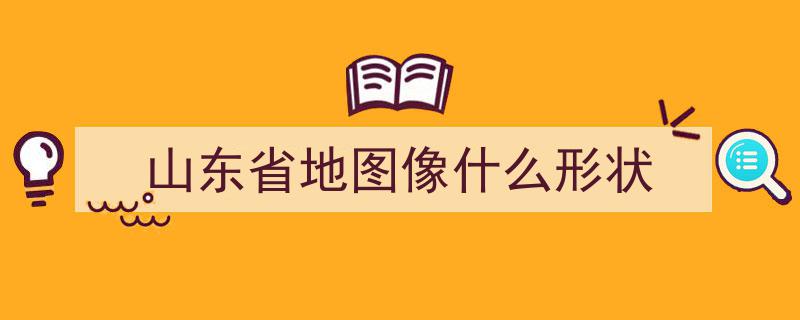跟人一聊起山东,有人第一印象是济南的大明湖畔、青岛的啤酒节,提到菏泽,多半是“一脸疑惑”,仿佛那只隐在地图边上的老猫儿——存在感不强。其实要搁在老辈人嘴里,菏泽这地儿,风水轮流转过不止一次,数百年前可是兵家踩踏过的热土,有那么点“天下围绕我转”的劲头。别看现在这片地方名气略显寂寞,好汉、枭雄、草莽、才子该有的角色全凑齐了——孙膑、吴起、吕后、宋江这些名字,搁谁门口挂出来,脸上都能沾点光。可惜历史冷暖朝夕,鼎盛的气象在柴米油盐中慢慢成了记忆,曹州府的旧日烟火,如今多半只剩下史书里的一抹旧迹了。

说起来大城市兴衰变化,不比咱小县城关起门来过日子,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把火一起烧。清朝后期,火车这玩意儿刚冒头,大伙都看着铁轨的朝向想着发家致富。菏泽当年那可是被选进省里头的济南到开封的铁道规划蓝图里,准备东接西联。谁料变数横生,一张纸画个路线说容易,铺起来不知多少难事,最后铁轨没招呼上门,菏泽的那点起势直接被掐了脖,经济命脉像是被冷落了的亲戚,眼睁睁看着旁边老邻居发达起来,自己只能干着急。
到了二十世纪乱世,那一段时间的菏泽更像城头变幻大王旗。抗日、解放那几年,很多咱们见过的大区换过名换过管辖,划来划去就像过家家似的。你比如说,原来菏泽下管的十多个县,到民国乱糟糟那阵子,变得只剩五个。原因倒不难懂——鲁西南这地儿当时成了革命根据地,又是国共鏖战的前线,兵马频繁,地图都没完没了地改,群众下地干活儿睁眼闭眼可能就换了领导。像朝城县,原本和菏泽还是一家人,后来就各奔东西,再没捞着过问温情。

建国后那会儿,菏泽迎来个新转机。新成立的平原省给了不少资源,县区数儿一口气就壮大,为啥?布置发展的棋子得按政策下,甭管是南旺县还是郓城、曹县,全都凑到一块儿,像是过年团圆饭,谁都不上桌心里不得劲。那阵黄河还是咱们最调皮的邻居,爱哪儿流就去哪儿,搬家一般跟着河道划界,像濮阳原来属菏泽的地,被黄河这么一横,直接换了户口本儿,变成濮阳专区的了。甄城县的县城其实不是啥新茬,是原先的濮县大名鼎鼎的老城,黄河水一轮,老家伙就只剩废墟,后来凑合着当了新县治,那股“因水而迁”的滋味儿,搁今天也是一段佳话。
当然,行政区划这口锅,谁都想少背点事。1952年那会儿平原省说撤就撤,菏泽又被山东收编,等于回了老家。唯一特别点的,是东明县被划给河南,干嘛?其实还是那会儿西北八县来回换地盘,边界画来画去,变成河南的一部分也就顺理成章。

别以为这就定下来了,风水轮流,1953年湖西专区撤掉后,菏泽又分到新地皮,单县、巨野啥的都划过来。新县像复程,活没几年,说没就没,被拆分归并,县名都快没人记得。1958年赶上全国大合并潮,菏泽干脆和济宁拉成一块,十把个月合着过,县区没少折腾。像定陶,名单上一划就没了,1961年又冒出来,县名在人事不在,回归那一下子也没哪家百姓能置身事外。梁山县倒是有意思,1959年才算正式地进了菏泽大家庭。你可能很难想象,短短几年一个小县的行政隶属能变三四回,平阴县甚至在菏泽底下叫了年把多就又离家出走,不禁让人感叹:县道如棋局,咱平头老百姓也只能随大势颠沛流离。
江河有情也无情。1963年时候,因为一条金堤河,大动干戈,山东跟河南你给我一点、我给你几片,各让一步才算息事宁人。东明县就这样又换回山东怀抱,河南那头没闲着,把东北角插进山东腹地,地图形状就跟一把斜插的匕首,至今看着都别扭。县与县的人口、地界一次次拆分合并,每一次变动,地头蛇得换一拨人,老人常常一夜醒来讲:“咱又换了省,孩子们以后记住,新隶属是啥。”

这之后二十多年,菏泽终于不怎么折腾了,地区、县区格局相对稳定,持续了二十来年,都说风雨过后见月明。可真到了1989,梁山县又离开了菏泽,算是命运里的一丝叹息,谁都没法强留。
变化最大的还要数新世纪,2000年,菏泽彻底改成了地级市,这个节点像道分水岭,再也不是昔日那个总被别人拿来“试刀”的专区了。城区一分为二,老菏泽市换了牡丹区的名字,多少有点给自己正名的意思。时至2016年,定陶也变区了。这一路过来,七县两区,走到今天这一步,说句老话,风水兜转,再炫的日头也有西落时,可但凡菏泽的根脉还在,那些老人物的故事,没准哪天又能泛起一层涟漪。

其实说到底,不管地盘怎么变,县名如何拆了又合,菏泽这一带的老百姓始终都是那一拨人——地头土著、祖坟根下长大的脸面。正如有人调侃,“行政区划变得头晕目眩,咱们种地娶媳妇生孩子,管它归哪呢?”但转过头来,老街坊间的乡音、老祠堂的榜文,还是能听出往日那些风云人物的余响。或许哪天,时间会拣回一张泛黄的照片,又把这些古地新人的命运拉在同一根线上。
人生百态,地方兴衰,有时不过一线之隔。菏泽的故事,兴许还会继续。谁晓得,等下一个大时代猝不及防转角处,是不是又会多出一个敢和孙膑、吴起叫板的名字?谁又能说清,哪一次小小的划界,终会决定一代人命运的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