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地图,就像家里老相册,每隔几年翻出来一看,照片里的人变了站的位置,有的笑了,有的不见了。80年代初那会儿,谁也没想过以后地名会折腾得这么花。十三个地市,都是“老伙计”,你叫得出的市、地区,基本当时也还是那个模样——济南还没“扩容”,青岛也没那么大气派。可架不住时代的风一吹,城市名字、辖区,十年八年就能变个新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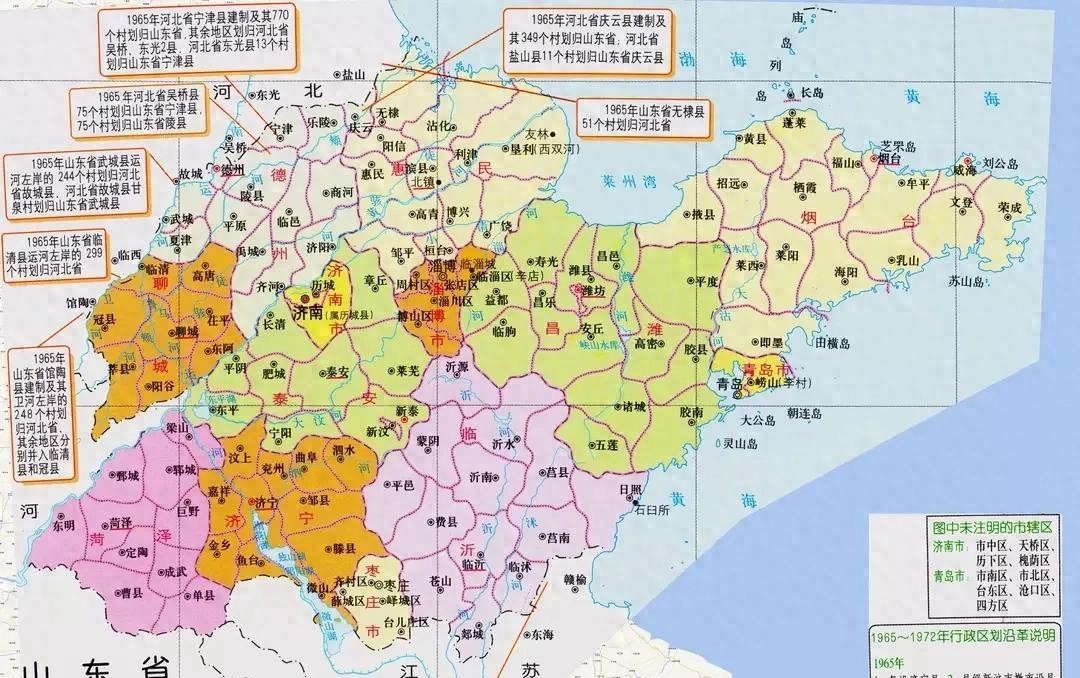
一开始,这事和胜利油田有关。1982年,东营市这个名字算是突然蹦出来——其实本地人心里多少有点复杂:咱家原来属于惠民地区,忽然就成了新生市民。这是油田专门“拉了个家”,垦利、利津、沾化和博兴的边角地头全拨过来了。只是头一年刚成立,广饶县有点“犹豫”,但很快也跟着划到东营旗下。1983年东营正式挂牌,那天油田的技术员还说,城市像井口一样,是冲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
我认识的许多老人,聊起这段,“东营那年成立,家门口修路,铁皮房子隔出来个办公室,听说以后上学要认东营。”其实不少人心里犯嘀咕:这新名字能像济南、青岛一样“响”吗?可没过几年,厂子建起来,油田的工资,东营就嗖嗖冒了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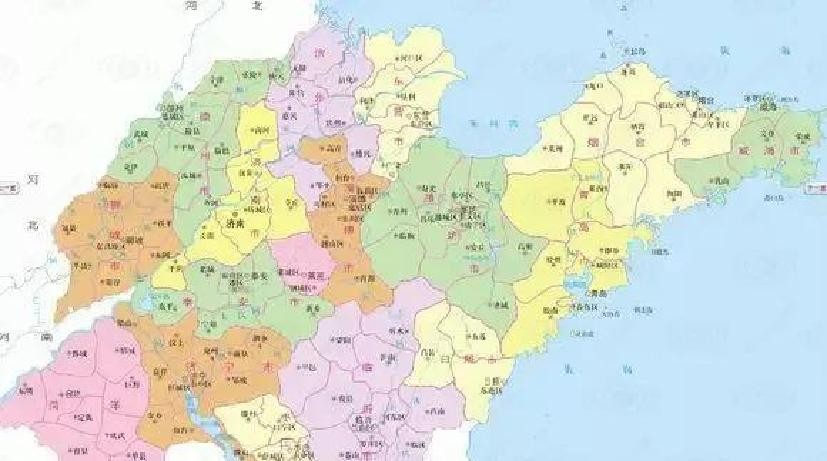
再后头是威海。1987年那会儿,烟台的崔老师说,“威海自己成市了,咱这里又得重新办手续。”县级威海市连着荣成、文登、乳山三县,突然就成了“正二八经”的地级市,原本烟台管着的地方,一下让出去了。县级威海市改成环翠区,荣成、乳山在过后几年又变成“市”,文登后来是撤县设区。感情上,有点像家里的老房分出去,当初都一个门口,现在拆成好几间。
那一路的变化里,少不得一些小人物的烦恼。比如荣成的王大妈,念叨过:“以前上头是谁都随便说,现在去市里办事,连车站都换了。”可也有年轻人觉得新鲜,名字变了,“升”一级,连相亲都多了点底气。

日照这地方,也是曲折。1989年从临沂里分出来,自个儿成了地级市,初时还只有一个东港区,后来(2004年)才又有了岚山区。辖区调整,说白了,就是拉着五莲、莒县,把地图又捏了一把。有时候家门口突然改了称呼,村里老人说:“还是临沂亲。”但年轻人头一次听见“日照市民”的称呼,憋不住笑,觉得自己“赶时髦”了。
再往后是莱芜。钢铁立市,这词听起来挺带劲,实际当时人还觉着:“有嘛头?”莱芜钢铁厂扎在那里,省里的官员也一头汗,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捧出来。莱城区和钢城区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眼看着地位提升,里面的沂源、新泰也各分了一块。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升级像门前装个新门牌,心里到底高兴还是忐忑——谁不好说。

山东的地名还有种“集体升迁”的热闹。80年代到2000年这趟大潮,九个地区陆续改地级市,可谁又料得到,名字后的故事都拐了几个弯。1983年一下子改了仨,烟台、济宁、潍坊先“打头阵”。烟台原本是个县级市,“升”了之后,芝罘、福山各自成区,潍坊那边也是乱成一锅粥。你问老城区的人:“你家是哪?”他得琢磨半天,最后说:“坊子老楼。”
再隔两年,泰安也改市,原来的泰安县变两个区。县里人说:“咱这地盘,过去谁都能去,现在往岱岳跑不带回头。”平阴、汶上、泗水这些县,也此消彼长,像是邻居家的孩子跳来跳去。这三地迁划,有种搬家的尴尬,大多数人看地图,能指得清自家,到了派出所却说不明。

时间转到90年代中期,轮到临沂和德州。1994年一下接连两市改格局,老菏泽人说:“心里总感觉这张图还要变。”德州变成地级市,大家奔着德城区,想的是省城那一套做派。可是新成的临沂,兰山、河东、罗庄几个区,互相之间还喊过去的地名。谁要真较真,外地人都跟不上。
聊城、滨州、菏泽几家在最后几年抵达终点。1997年聊城升级,东昌府区成了“城里”,嘴上沾点光。到2000年,滨州、菏泽把地区的名字彻底变成地级市。这后头,原菏泽改为牡丹区,听着确实好听。有菏泽老街坊笑话说:“牡丹名气大,菏泽人气更大。”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全省就有十七个大市。有几年购物、跑单位,大家心里都有点飘:“到底这地方以前叫什么?划给谁了?”2018年莱芜并入济南,莱城区、钢城区换了新门牌。有人说莱芜终于成了“大济南人”,也有人摇头,“说不清还是家里那块水土亲。”
如果你站在老青岛人旁,他或许会感叹:“这些市,名字一年一变,老记不住。”但也许,一张山东地图、十六个地名背后,藏着千万老百姓的喜乐忧愁。城市是会长大的,也会流汗、改名字、吵吵闹闹。或许我们更关心的,永远是家门口的那棵梧桐树,和它旁边老人晒的麦苗。
这么多年过去,地图上的方框越画越实,人心里却总还有点虚。究竟一个市的故事,是地名,还是那一年午后,谁家灶台边的热气?这事,真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