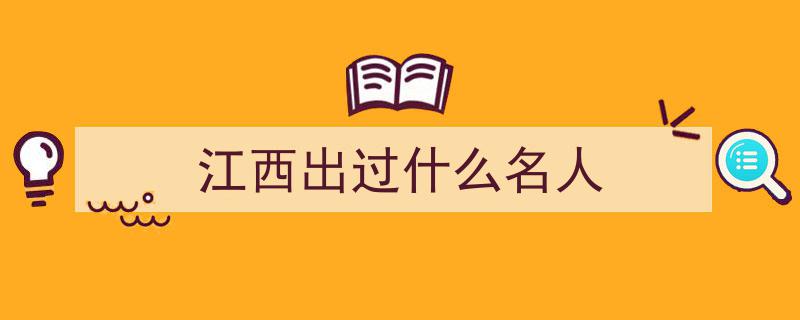要说咱江西人,骨子里总带着几分傲气。可但凡和外地人闲聊起来,赣州这仨字儿总是头一回被抬出来——甭管吃饭、喝茶,或者就是在菜市场唠嗑,都有人唠叨:江西的赣字,不就是从赣县冒出来的么?赣江的源头也是那旮旯儿,从古到今,不光山水美,人也灵。别说咱吹,这儿出来的大人物,隔三差五就能数上一大溜,把人听得直咋舌。至于什么“江南第一宋城”、啥啥“东方古罗马”,你在外面听多了都觉得这些名头有点玄乎,可老一辈子都爱说,赣州这地,书生气和人情味都稠得很。今儿,我就跟你摆摆赣州那些个响当当的人物,说实话,这里面不少传奇可比电视剧还带劲。

咱先从老钟家说起。钟绍京,这名字听着有点生分,其实你只要去过西安看大明宫,或者北京那帮老建筑,部分匾额上那种规矩的楷书,说不定就是他的手笔。后世学书法的,一提唐代名家,除了欧阳询、褚遂良,就得落他头上。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人家钟绍京当年不只是毛笔玩得溜,他在武则天朝里还做了大官,连皇宫门口的金漆匾额都特许让他题。武则天那个性格多强势?可就是偏偏欣赏钟绍京的字,传说每逢宫里大典,人家亲自吩咐:“让钟绍京来题门匾。”外臣进宫往往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的字。有一回北门房梁塌了,掉下来一块木匾,还没碎,宫里太监眼巴巴地捡回去,说得修好再挂,因为那是钟大人的手笔。
不过老天爷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等武则天去了,宫里的当权大变天。中宗李显继位结果被自家媳妇韦皇后一顿作妖,连自家女儿安乐公主也来掺和,闹得朝堂鸡飞狗跳。眼瞅一锅粥谁撑得住?偏偏钟绍京不含糊,带着自家两百号人跟着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和太平公主一路冲宫,当年大明宫的太极殿金瓦下可真动了真刀真枪。外头都传李隆基机警,但真打进宫那一刹,是老钟在侧刀枪护主,砍翻厉害的侍卫。他没留下什么血书,这一仗,直接卖命陪了皇子。不光朝堂留名,后来朝里升他当了宰相,还封了个越国公的爵位——可是官场哪有那么安稳?偏巧赶上同僚姚崇也是个拧巴脾气,两位大佬正面刚,谁也不肯让步。到了李隆基真做了皇上,反而被贬去了闲差。可别以为旧官僚都结恶缘,据老城坊间传说,钟绍京离世八十七,家族兴旺,赣州人提起他,还得路过老祠堂时,暗中肃个立。

聊完钟家,再看陈氏一门,那可真是赣州人的门面担当。其实,北宋那阵儿,石城的陈恕是出了名的“会算账”、“能理事”的大能人。流传最广的,还不是那一摞功劳簿,而是一句坊间顺口溜:“天下盐铁,真成陈恕家私。”宋太宗欣赏他,书案亲题“真盐铁陈恕”,直接钉在大殿柱正中,说这是国库的定海神针。别看那年头盐铁是国家命脉,碰得哪怕一丁点亏空当砍头,陈恕的账本却明明白白、铜墙铁壁。最有趣的还有一桩陈年往事,据说他父丧那年正闹荒灾,他非但没请假闭门守孝,反倒亲拎官袋走街串巷,一边赈灾一边安排伙谷,让百姓年年挂嘴的“老陈管钱铁账无亏空”——这不做作,赣州人性子里的靠谱。
陈恕办事稳,识人也精准。他曾经一口气把三十八个有志青年送进翰林院,里头有四个后来都做了宰相。有考据的学者还特意翻过“大名府录用表”,发现最早一批外放知府的名额,都写着“荐自陈恕”。咱们常说世事一场大梦,元气归于陈门。后来陈家后代,陈执中更是做了仁宗朝的枢密使,说粗点就那会儿的军政总管。这就是“文治武功,两代传家”的老典故。顺便一提,宋太宗还操过陈恕的心事。听说他鳏居,没多琢磨,干脆把江南才女王氏指给陈恕做妾。一时间,洪州城头张灯结彩,连市井小贩都作诗调侃:“陈家曲水流觞夜,国主亲配闺秀来。”

有趣的是陈家的武脉也特别硬气。石城的陈敏,老陈恕隔着辈分要喊他“贤侄”,这陈敏打仗是真不怕死。绍兴年间,金兵南下的时候,朝里文官还在商量“守还是打”,陈敏已经穿盔甲领兵上马。他常说一句话:“兵贵神速,守必为功。”有回金兵佯装投降,全城都在庆祝,独他一人冷着脸说:“别高兴太早,这事不吉。”果然夜里金兵撒野,他翻身上马带队劈杀——平时脾气不大起,真到出兵,街上的孩子都知道“陈大人骑红马过城,金人要倒霉”。他不仅守住了高邮、楚州,还从家里掏银子修了十二道石坝,硬是把农田和防御一块抓起来,凭着这些手段,才有了后来人称“银铸城”的美谈。老百姓流传着,“宁给陈大人种田,不做别家义兵”,因为跟了他,家小有饭吃,兵也有盔甲穿。
你要问赣州到底书卷气有多重?说起来,南康的綦毋潜,你或许没啥印象,可翻开《全唐诗》,哪哪都有他的影子。那年头诗人多得是,有能耐被王维称兄道弟的,屈指可数。綦毋潜和王维、李颀、卢象、甚至后来做了宰相的张九龄,全都是酒杯碗底论诗才的老朋友。有一次王维过南康,看见門外杨柳正青绿,非要拽綦毋潜去江边写诗,俩人坐了一下午,抄出来的诗稿还被邻居抢去传阅,成了社区的口头话本。

綦毋潜在朝中做过右拾遗、集贤院待制,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文史顾问。安史乱世爆发那年,李白因支持靖难被流放夜郎、客死他乡,杜甫千里颠沛,壮志未酬。倒是綦毋潜见风不对,老早辞官退隐,把官印一丢,盘缠备好,说是“避乱江淮”,从此无踪影。后人感慨,诗人盛世,常常难有好结局,反倒这位南康才子,活得潇洒自在。
赣州家族式“团体出道”的还不少,比如虔州的章贡四曾兄弟——曾弼、曾懋、曾开、曾几,咱看今天谁家能出一个高考省状元,已经要放鞭炮,宋朝那会儿,他们家连中进士,一个兄弟是陆游的老师,另一个和杨万里论诗,每年家里中秋都要开诗会,还请周敦颐一块儿凑热闹。老家门楣还挂着手题联:“五子登科,四海留名。”这些故事,你在赣南一些老祠堂里的木牌匾上还能隐约看到凋残的字迹。

讲到宁都,那还得提谢元龙,人称“状元谢”,是出了名的高龄才子。都说古人状元多十八九,谢元龙偏偏五十九才高中。与此同时,文天祥那股子少年意气还时常约他练武,说“谢老哥,诗我能背,刀你教教我。”谢元龙不仅能写诗,弄枪使棍也在行。元兵打到江西时,他负责襄阳军粮,城破后也没投降,自个儿倒扛一把剑杀出重围——后来一辈子归隐山林,村里孩子们见了谢爹都要行大礼。一直活到八十多,村口石碑上的“状元谢墓”如今还在。
池梦鲤的忠义可和文天祥齐名。南宋灭亡那一年,赣县老人还会跟后生讲“池公名榜第一,忠勇千载传”。他和张世杰撑着南宋最后的防线,元军压境也没逃避。后来他牺牲在征战之中,乡亲们扛着棺椁穿林度水,找了桃源洞给他安葬。乡里老太太说:“状元池生前没留下几桩田地,忠心两肩挑,咱后辈可别丢了风骨。”

还有大余戴家“四进士”,戴衢亨一生几起几落,嘉庆皇帝那会儿让他做体仁阁大学士,这可相当于宫廷的首席智囊团长。家族里父亲、叔伯、兄弟全都科第出身,比起今天清华北大一家四口,戴家人可把老大屋子都挂满功名匾,庙会上小孩子都得学着念“戴公堂联”。
最后,说赣州状元,老一辈人总不能不提郑獬。这位算得上北宋仁宗时期最风风火火的文官。当年英宗让他做兵部员外郎,文人里头真有胆气的。他担任杭州知府时,敢当面怼王安石的新政,替江南百姓争说好话。当年他写下《郧溪集》五十卷,虽然后头丢了好多,可今天只要在宁都的祠堂里,你还能看见后人写的“义夫宗师,风骨长存”。

说归说,赣州人乡土情结都挺重,讲这些祖宗故事,更像给后辈点一盏夜灯。你要问还有那些赣州的传奇人物吗?我猜你翻一翻本地老祠堂、大庙前的长石板路,还能踩出一堆故事。至于哪个最叫得响,恐怕只等有那么一天,咱再围着桌子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