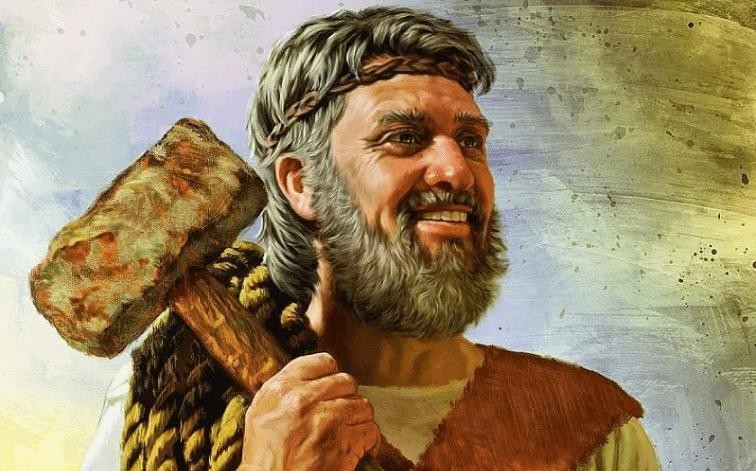谁能想到,连一只羊的名字,都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面子和命运呢?我们常说“名字不重要”,可如果连身边的生灵都叫着别人的名字,总觉得哪儿别扭。说起来,这种“叫错名”的事,其实不只是曾经发生在遥远的拉美印第安人身上,也实打实发生在你我脚下的土地上。

话还得从南美一位著名作家加莱亚诺小时候说起。这孩子上学时贼聪明,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欧洲探险家巴尔沃阿首次站上了巴拿马的高地,一眼望见大西洋太平洋“两海相映”,历史性一刻。加莱亚诺忍不住举手:“老师,那住了成千上万年的印第安人都瞎了吗?”老师一愣。全班都愣了。这问题,不大不小,像一颗小石子扔进多年平静的湖心。
说回我们中国的事。1997年,摄影师葛玉修在青海湖边花了半辈子扎堆野地,苦苦守候当年几乎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某天,他终于等来了个“新面孔”——普氏原羚。那一刻,心跳差点快过相机快门。他当即写了篇文章《救救我吧,普氏原羚的呐喊》。没想到,文章一传到本地,青海人却一脸懵。啥普氏?那不是咱土话里的“黄羊”吗?同一种羊,亲眼见过,甚至小时候跟着打草的老头儿认识它们比认识隔壁小孩还早。可偏偏,科学界给它起了个比隔壁小孩还陌生的“洋名”。一时间,羊还是那个羊,人却仿佛成了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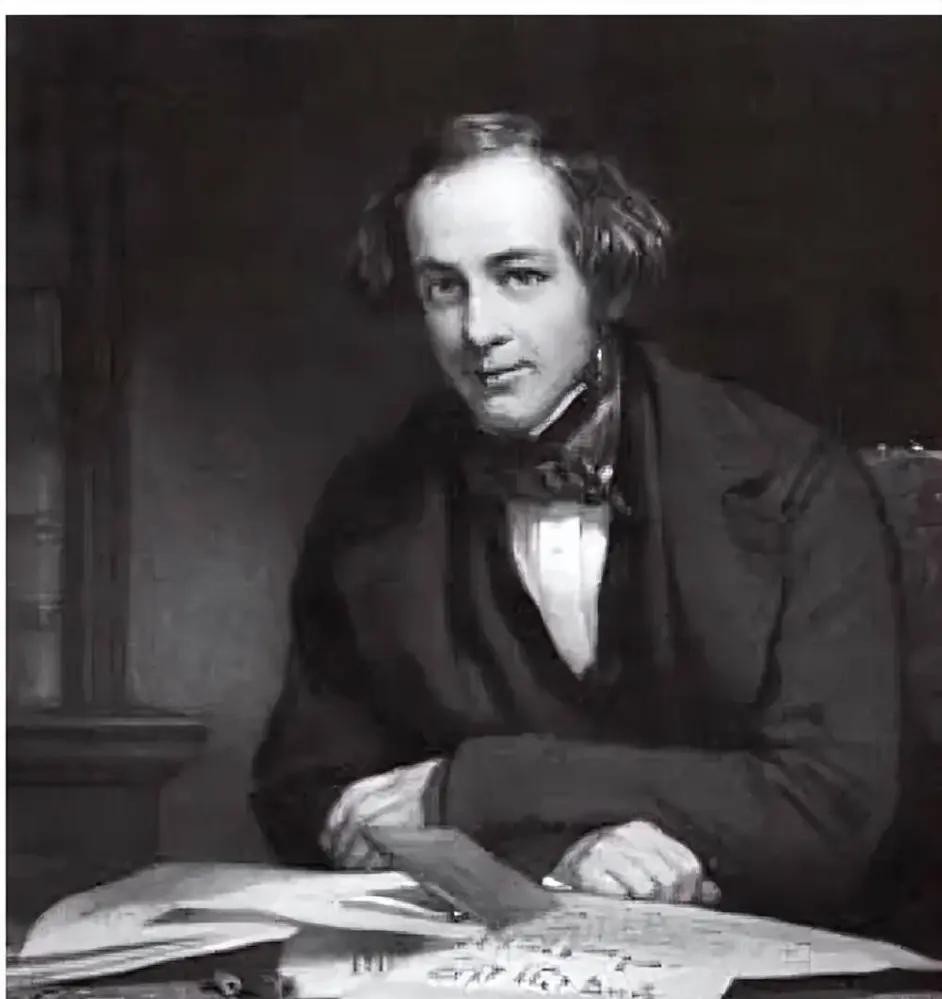
很多人不知道,这羊的正儿八经学名——“普氏原羚”,居然是个俄国探险家的姓。普热尔瓦尔斯基,19世纪风风火火扎进中国,带走了无数“新奇”的动物标本,然后冠上了自己名字。你瞧,那会儿玩动物名的人,谁先把证据装进皮箱,谁就能拿张命名券。这种事,不止发生在黄羊身上。什么“普氏野马”“普氏裸鲤”,都是一个套路,成了“中国物种”的盖章,也成了普热尔瓦尔斯基这些人的荣誉榜。
其实不只有他一个。比如麋鹿,世界有名的“四不像”,咱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在诗经里写过。但现在国外科学家见到后,说那是“大卫神父鹿”。又比如中国上千种鸟,绝大多数的正式“学名”都挂着一串欧洲姓氏。仔细一查,真正由中国科学家来命名的鸟类,竟然就那么三种!这就像自家孩子,全国各省有自己的小名,户口本上却签名盖章,全写的是外地人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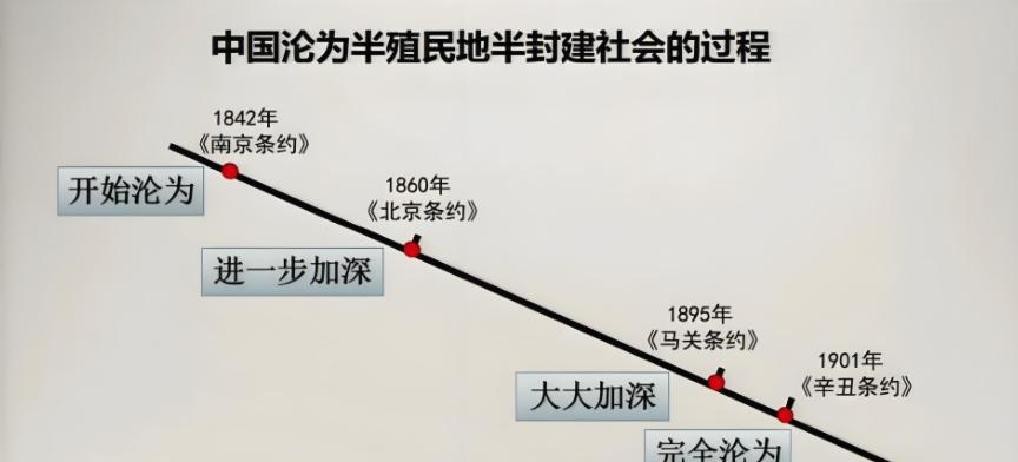
不过老实说,这么闹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打开动物学那本“国际手册”,里头一条条规定,拉丁文先行。时光回溯到18世纪,瑞典的林奈先生一锤定音:谁捡到第一个“模式标本”,谁就有命名权。动物命名,不是看谁家发现得早,而是看谁能把它包装进科学圈。你给它起名字,人家也给它起名字——最后,写论文的拳头硬。
更揪心的是,就连家喻户晓的水稻都沦陷了。咱中国人用水稻养活了几千年人口,但要分学名的话,现在管它叫“日本稻”“印度稻”,中国水稻反倒成了“无名英雄”。哪怕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耕作,到了学术那层面儿,种田人的贡献就像漂在稻花上的轻尘——一阵风吹,啥也不剩。

这样的“洋名风”,其实远不止动物植物。你如果学数学,八成也听说过什么“毕达哥拉斯定理”(全世界的初高中过关斩将的孩子得背),我们叫“勾股定理”。可偏偏全世界都记得毕达哥拉斯,几乎没人提中国《九章算术》和祖冲之之子祖暅搞出的“祖暅原理”(最后统统叫成了“卡瓦列里原理”)。有时候,历史绕了个大圈,最终功劳簿上只有“外来户”。
话又说回来,这世界命名规则到底是谁制定的?林奈的拉丁分类只是“表面”,更深的理由其实没那么难猜。想想,当年欧洲人出海远征,夺地拓土可不是为了和土著一起分享荣光。身体上占了便宜,法律上写了条款,还要再来个精致的精神占有。“命名”本身,就是在立规矩。你越是随口叫得顺,背后其实是承认了对方的标准和规则。久而久之,本来生活在这里的你,仿佛也是“外来者”的见证人。

命名不仅仅是叫法,其实也是占有。英国跑到美洲去,一边画地图,一边压着原住民签合同,然后再一套宗教洗脑,精神阵线再扩一圈。欧洲人来中国呢,传教士更爱从“精神入手”。他们进了大山,走遍村落,然后一边写信一边写学名。每到一处,记录的不是当地人口中的“山鸡”“灰头燕”,而是拉丁字母里的“大卫神父鹿”“普氏原羚”。看上去挺洋气,本质上也封了他们的“文官帽”。
那为什么全世界都接受了这种做法?说白了,谁制定游戏规则、印发学名证谁就坐庄。有人会说:外国那套规矩总方便啊,科学嘛,讲究国际统一。可问题是,林奈这套起名法儿,从头到尾都没说要照顾动物本身的特征,反而总想着怎么把“谁发现了谁”“谁捡到了第一根羽毛”写进后人记忆里。名称越来越不着边际,动物的模样、生活环境倒成了次要。这么玩下去,到底是敬畏自然,还是给自己脸上贴金?

当然了,也不是说外来的都一文不值。科学的大门又不是只能开一扇。可气人的地方恰恰在于:时至今日,哪怕中国本地特有的动植物,名字都有“洋味儿”。家门口的事,话语权却一点点滑向了远方。葛玉修当年在青海写到“普氏原羚”,现在这只羊也总算有了自己的“中文身份证”:“中华对角羚”。但类似的事,还没完。
吴觉农讲过一句狠话:“一个国家落败到什么地步?就连土地上长的、空气里飞的,都能被人‘收编’成外国户口。”想想看,哪怕你是一只千百年来在中国奔跑的黄羊,命运也逃不脱纸上的那一行“他人的名字”。

如今网上总有人说,落后未必挨打。可事实往往给了这自信一巴掌:生活里,名字、制度,是随风转舵;可精神上,往往最难翻身,最易久困藩篱。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让自家孩子、家门口的动物、草原上的风都叫回自己的名字,也许不止是语言的胜利。那是认回了自己的土地,也认回了自己的骄傲。
故事没完。也没那么简单。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掌握了命名权,哪怕不再用拉丁文包裹,能不能让“中华对角羚”这个名字,走进更多人的心里,而不只是纸面上?也许,才是真正的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