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核有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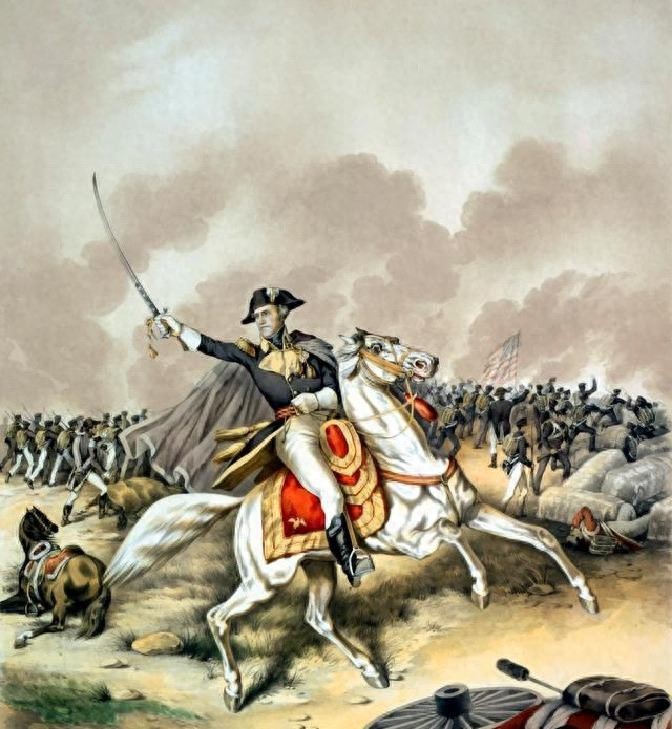
编辑|大核有料

1756年,巴黎春意还没转浓,欧洲大陆已暗流汹涌。七年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法国财政官们皱着眉头,可更多还没意识到后面风暴的重量。战争持续七年,但这种战争压力就像雨季,越往后越潮湿粘稠,渗进每一张银票和田地。外头打仗,国内钱罐子却越来越浅,眼瞅着底儿都快看见了,这账你说怎么算得清楚?有人拍桌子,有人摇头叹气,他们争来争去,最后还是骑虎难下。

财政问题不是今天才有,法国自路易十四时王室挥霍就埋下了隐患。税收方式老旧,贵族和教士拿豁免当家常便饭,自己富得流油,农民却一身债一身汗。全国三分之二的税,全都落在老百姓和市民头上,且不说公平,征税效率也一塌糊涂。听说,有的地方收个税需要用三个官吏,一个记账、一个核实,还有一个盯着同僚不偷拿。可最后到国库的钱却少得可怜。

七年战争突然加速了窟窿的扩大。法国为守住全球的脸面,各地殖民地、海陆战线都投入巨资,每打一仗就像往火坑里扔黄金。1758年,仅军费一年砸下两亿利弗尔,后头还有东印度公司等半官方私人财团薅国家羊毛。到1760年,法国国债暴涨七亿,三分之一预算用来还旧账,走一步看两步,叫谁都心慌。

有人说,法国当时不是没有钱,是钱在贵族和教会口袋里没动。事实恐怕比这还复杂,宫廷宴会一桌流水席,外面苦营兵却拥不上棉被。有官员借军需采买之名大肆揩油,武器买回仿佛绣花枕头,外表光鲜,实际上打了也不中用。财政大臣反复设想改革,或增税或引进新税种,如专利税、消费税,但反响极其恶劣——城里铺户拉起横幅,乡村农民到巴黎游行,全社会躁动压根儿停不下来。那星星点点的抗争,有的像火星,有的像水泡,但都在膨胀。

据当时知情者记载,法国政府为应急借债,短短几年发行公债,总额比法国两年税收还多。债主多是贵族和金融商,手握借据敢跟国王叫板。这些钱虽能解一时燃眉,却埋下更大窟窿:利息越滚越大,财政官员夜里都睡不稳觉,左边床头账本,右边枕着法典。政府几度试图改革财政体系,搞什么“土地登记法”、查账“肃贪清查”,可改革还没落地,官僚集团就先互相告状,方案都懒得具体执行。

经济学者最近通过法国国家档案局数据交叉了那几年收支表,显示1762年国家赤字突破25%,其中“管理腐败”类账目模糊到让人发指。想想也是,社会只有一小撮人不纳税还领津贴,剩下人却喘不过气。商品价格逐年飞涨,老百姓今儿种麦子明儿就亏空,有的工坊两三天就倒闭一间。那时候,你要买匹马,三天价格就变一回,猜不准明儿还能不能喂饭。

法国社会因此被撕开一条缝。镇上裁缝喊穷,农家老妇和巴黎律师同进同退,不满渐渐聚拢。新闻笔记上偶有讽刺,对贵族插科打诨,对财政大臣胡乱吐槽,风气之坏倒没人拦得住。至于改革,才引进一点新鲜血液上来,旧系统就像老树顽抗一样,把新芽都掐死了。曾有财政御史私下暗骂,法国这条船全是漏洞,补不胜补,到头来要翻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

也有人认为,那几年并非毫无转机。有知情者披露,1763年战事告终后,总理大臣曾短暂恢复一部分财政能力,成功收回了一部分殖民地赋税权利,甚至减少了奢侈税。但现实摆在面前,这点回流如牛毛入海。战争影响没有那么快消褪,国库依旧空虚。有说法称法国财政体系其实没全坏,也有人死咬着说,根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表面体面都是装的。

战争结束没几年,利息账单像打鼓一样拍门。农民一茬接一茬破产,农用工具当废铜卖掉,家里连面包都靠救济。而此时,财政官员仍在议会楼高谈阔论,编预算时用“假设收支平衡”塞进条款。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社会罢工大潮蔓延,失业人口逐年上升。数据在巴黎高等法院的卷宗里写得清楚:1765年,巴黎城市失业者突破10万,财政窘困加剧社会矛盾,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不过,也不是没人努力过。财政大臣蒙凯尔姆试图引入更精准的征税体系,和新一代会计合作,把账是做细了。可是税收落实记账刚两年,有的基层官吏单独拎走了半数收入。巴黎大法官甚至说,国民税负已经如同脖子上的绞索,谁敢再勒紧?但负债越来越像枷锁,没有多少人敢真松开手,生怕全部断裂。

到1780年代,连国王路易十六都不得不承认老办法行不通了。三等阶层和普通贵族站到街头,呼吁公平新法。那个场景,街道两旁全是挤得黑压压的人,议员们台上吵成一团。你说他们真懂什么财政政策?也许懂,也可能装懂。旁观者看热闹,谁在乎税收条款背后到底有多少水分?

历史档案显示,七年战争几年账目留下的窟窿,后来怎么补也补不上。增税、发债、紧缩开支、财政刺激,一样样全试过,但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同债务一道滑坡。新的改革法案出来,第二天反对声就满城飞,而掌权者犹豫—也许是故意的拖延?天知道。直到1789年,财政危机终于彻底爆发,三级会议变成全民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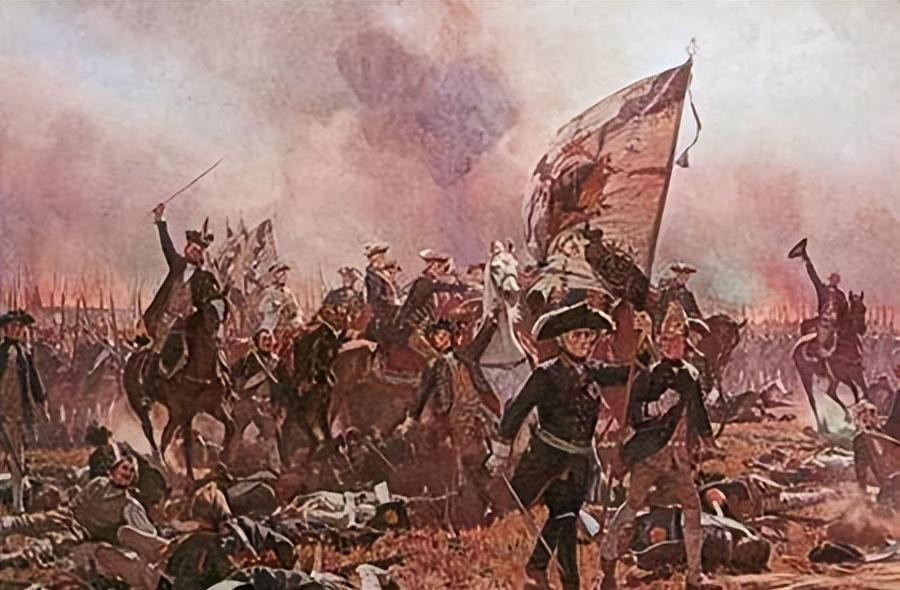
有观点说法国走向革命原本是避免不了的,说到底,财政危机只是导火线。可实际情况又不像一根线那么简单,层层纠缠,早已搅成乱麻。昭示着再多教科书式的总结,都不如一场粮价暴涨和百姓骚乱来得直接。城市里有小贩,乡下有佃农,满城风雨,因为没钱。想拦得住?几无可能。

再说社会影响,贫富差距肉眼可见,现实是贵族夜夜宴饮,农庄里老人孩子瘦得皮包骨头。那时有旅居外国的英格兰人写信回家,说“法国的穷人像陷在泥潭,根本没法自拔”,写信的人倒未必真懂全貌。还有本地律师在球场抗议,讽刺国王钱花得像撒豆子,却不愿为老百姓多买一只面包。看起来荒谬,其实他们心里也没谱。

以上事实若说全是历史必然,按理有些牵强。毕竟,1760年代初巴黎一度经济短暂复苏,商人觉得世界还没散。但刚一喘口气,利息账单又压得喘不过气,朝野又分成两派,来来回回没个头。

回头再说贵族,舆论中骂他们冷血。但他们有时也受影响,不少小贵族因投资国债损失惨重,甚至被迫卖掉祖宅以偿还贷款。有人觉得他们罪有应得,有人同情他们倒霉到头。可社会主流声音已经变调,没人指望他们再救法国。

冷硬的财政现实逼着社会沉闷地等待爆发。日志里记着,普通人偶尔也会幻想有朝一日能见到公平正义,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活着,拖着。政策一出,市井巷尾窃窃私语,有的人开始不信政府,还有人干脆置身事外,反正自家饭都不够吃,哪管几百里外的财政卷宗里写了什么。

所以说,七年战争不光是一场史书上的战争,也是法国财政史上的一道深槽。那些数字背后,全是哀愁和无奈——也可能有机会,也说不定全是泡影。最后谁欠了谁,国家又该如何修复?这些,历史没给答案。

就这么说吧,七年战争压出的法国财政危机,本来就是一券烂账,加点人心躁动、多几场权贵倾轧,一锅粥没熬好,溢出来了,谁也收不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