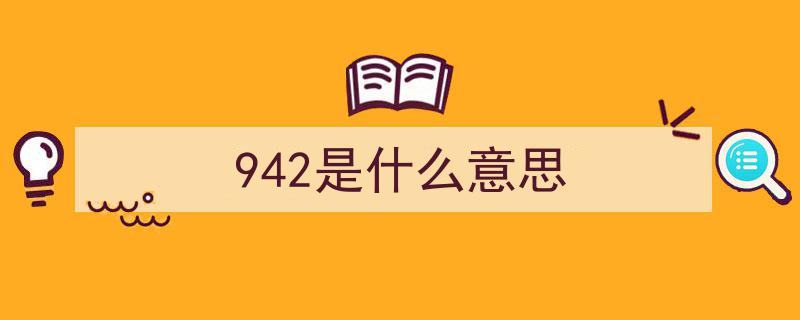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石敬瑭)
没做皇帝之前,石敬瑭是一个很节约的人,尽管他据有十分富庶的河东,但是他从不乱花钱,因为他很有危机感,知道自己早晚要和李从珂开战,所以他很喜欢积攒,攒钱,攒粮草,攒军械,攒兵马,日子用清贫来形容也不为过。
做了皇帝之后,慢慢的他就忘记了初心,生活开始逐渐奢靡,别的不说,石敬瑭居住的皇宫,随处可见,是黄金,宝石,玉器,那装修一看就花了不少钱。
刚刚开国的时候,后晋的都城是在洛阳,后来迁都到了开封,这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石敬瑭觉得洛阳太过破旧,不如开封繁华富庶。
做皇帝之前,石敬瑭勉强还算的上是善待百姓,但是由于他得国不正,做了皇帝之后,百姓们对他缺乏好感,反对他的很多,民间各地又起义不断,因此石敬瑭专门制定了非常多残酷的法律来镇压平民,搞出一些分尸肢解,挖眼睛割舌头的酷刑来,甚至还把活人放到锅里蒸煮。
因为反声不断,石敬瑭怀疑心重,他对武将不信任,因为武将总是造反,尤其是范延光和安重荣这么一闹,皇帝更是看谁都像反贼,至于文官,在五代时期从来也靠不上,因为他们的能量太小了,所以石敬瑭开始重用宦官,一时间后晋朝廷权宦当道,政治愈发黑暗。
做皇帝之前,石敬瑭是后唐的武将,当年后唐灭后梁,明宗取代庄宗,石敬瑭都是先锋大将,是屡建奇功,悍勇无比,但是做了皇帝之后,为了自保,为了享受现有生活,他开始卑躬屈膝的侍奉契丹人,他自己称呼自己是儿皇帝,尊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这就已经够屈辱的了,契丹的使者来后晋传达旨意,石敬瑭往往跪地受诏,那您想石敬瑭是皇帝,他都得下跪,那既然他都跪了,那后晋的大臣们也得跟着下跪。可实际上除了石敬瑭,除了桑维翰这种当年主张事辽的大臣们之外,大部分的后晋官员,他们打心眼里排斥契丹,你让他们跪,他们心里很难受。
之前后晋朝廷里有个叫做王权的兵部尚书,石敬瑭派他出使契丹拜见辽太宗耶律德光,王权耻于向契丹人下跪,坚辞不受,宁愿辞官回乡,也不愿意出使。
王权的情绪,其实是当时后晋官员的一个普遍写照。

(契丹壁画)
不仅如此,这契丹人还从来都是颐指气使,来了之后那架子摆的,那脸子给的,那就别说了,你石敬瑭是中原的皇帝又怎么样?说训你一顿就训你一顿,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听着。
我们想一下,石敬瑭曾经也是一代枭雄,如今做了傀儡皇帝,难道他真的甘心吗?
其实,石敬瑭也不甘心,有时候他自己没事也会念叨,说自己北边事之,颇感不快,在安重荣给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他甚至有那么一个两个瞬间动摇过,但是很快,桑维翰就把他给劝住了。
桑维翰给石敬瑭上了一封奏疏,主要内容是劝谏石敬瑭不要和契丹人交恶,不要开战,为此桑维翰还总结了七个原因。
第一,是契丹的实力强劲,土地广,人口多,装备精良,战马充足,连年征战人家都处于胜利状态。
第二,契丹状态非常的好,但是后晋连年内乱,士气低落,国库也比较空虚,民生凋敝,不是打仗的好时机。
第三,后晋和契丹曾经签有盟约,契丹人虽然经常跑来要钱,跑来耍威风,但是他们没有主动侵略过我们,我们却主动开战,在道义上吃亏。
第四,辽朝的皇帝不是善茬,不好对付。
第五,燕云十六州已经握在了契丹人的手里,我们在地形上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
第六,契丹骑兵勇猛,我们难以抵挡。
第七,称臣进贡看似屈辱,实际上是缓兵之谋,权宜之计。
最后,桑维翰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旧五代史·卷八十九》:然后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以俟国有九年之积,兵有十倍之强,主无内忧,民有余力,便可以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
桑维翰说,陛下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抚士兵,养育百姓,积攒人口,发展农耕,训练士兵,我们要积攒够用九年的粮食,要发展到比现在多九倍的兵力,要让国家内部没有隐患,民众团结一心,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等待契丹衰弱的时机,扬长避短,攻其不备,一定能取得成功。
看得出来,桑维翰的意思是,臣服契丹只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更长远的打算,总有一天后晋要消灭契丹,克服北方。
这话对石敬瑭很受用,何况他现在对契丹也有了不良情绪,你让他一辈子事契丹,他也未必接受的了,就算石敬瑭人实在是没用,他不敢和契丹开战,他也需要为自己这个充满了耻辱性的儿皇帝身份找一个说辞。
以前有人指责他事契丹人,他无话可说,他没法解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可以说,自己是在韬光养晦,自己是屈身事贼,这都是为以后做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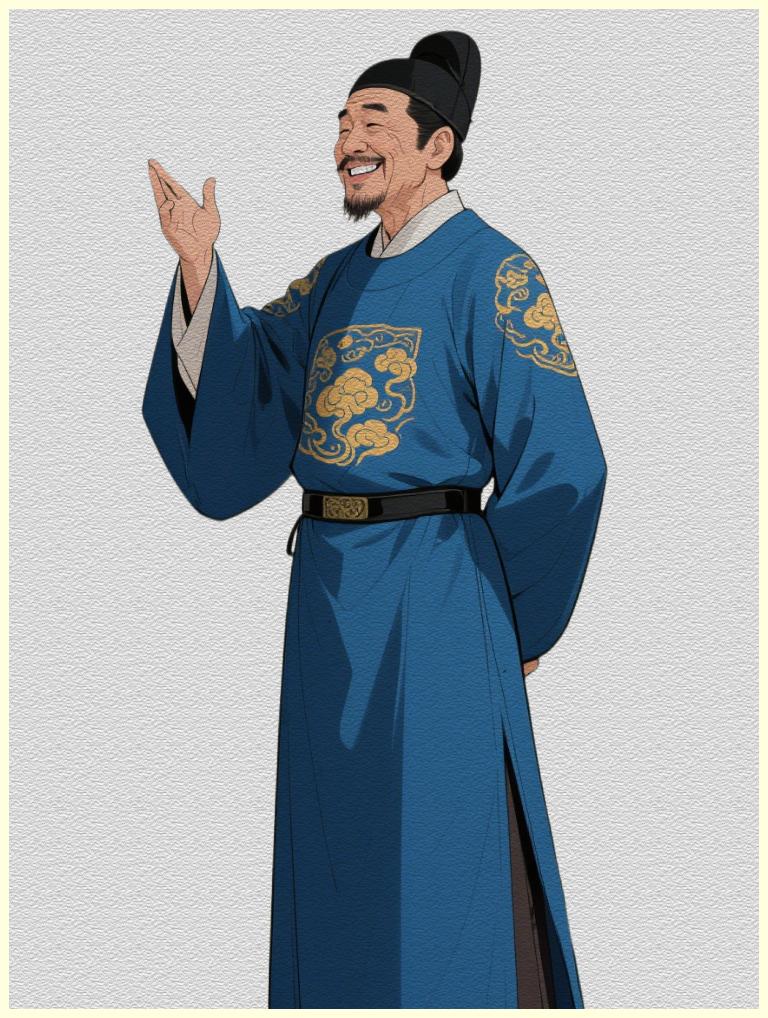
(桑维翰)
古人有云:
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桑维翰的奏疏,对石敬瑭来说,像一剂强心剂,也像一贴迷魂药,精准的扎到了石敬瑭内心最痒,也是最痛的地方,桑维翰为他勾勒的美好蓝图,给他的卑躬屈膝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以后他就可以说,朕不是懦弱,朕是在卧薪尝胆啊。
但是,君臣二人都知道,所谓蓝图,不过是一纸空谈,实在难以实现。
桑维翰说,要积谷聚人,要养育黔黎,首先想要做出这种事业来,你皇帝就得做出表率,你得节俭,可是你石敬瑭日渐奢靡,宫廷生活超支无度,一天挣一百,你敢一天花一千,你自己花钱如流水的同时,朝廷还要每年支付给契丹巨额的岁贡,这些钱从哪里来?自然只会从赋税中来。
沉重的赋税早已压的百姓们喘不过气,表面上说要“积谷”,实际上照旧是对民间进行疯狂的搜刮。
桑维翰说要强兵,可是这兵要怎么强呢?国库空虚,军饷经常拖欠,士卒不满已经是常态,更要命的是石敬瑭猜忌心越来越重,范延光安重荣的叛乱,让他对所有掌握了兵权的人都充满了警惕心,这样一来,他不仅难以放手,让将领们“训抚士卒”,反而处处掣肘,频繁的调动武将,甚至安排亲信宦官作为监军,因此军心涣散,战斗力那是不升反降。
桑维翰说主无内忧,这就更讽刺了,石敬瑭越是想用严刑峻法压制反抗,民间和地方藩镇的离心力就越强,因为他重用宦官嘛,这些宦官仗着皇帝的宠信,肆意弄权,贪污受贿,搞的朝堂内外是乌烟瘴气,说主无内忧,倒不如说是全是内忧,文官是离心的,武将是寒心的,契丹是压榨的,藩镇是做大的,梦想是遥远的,理想是破碎的。
说白了,都是梦一场。
何况,桑维翰的计划,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但石敬瑭的身体和精神,在屈辱,在猜忌,在巨大的压力下,很快就迅速的垮掉了。
长期的忧惧和内心的巨大矛盾煎熬着他,他变得暴躁易怒,身体也每况愈下,奢靡的生活没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反而加速了他身体的衰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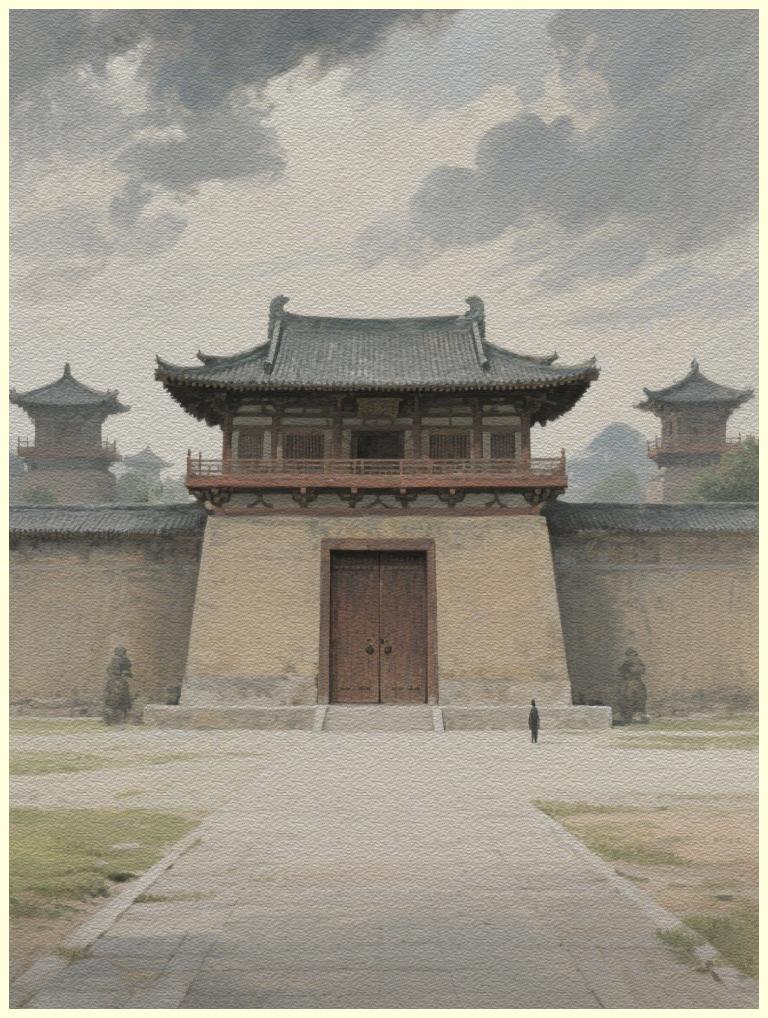
(王朝归路)
开封繁华热闹,石敬瑭躺在御榻之上,生命如风中残烛,华贵的寝宫里金玉满堂,却驱不散刺骨的寒意和无边的孤寂。
他或许会想起在河东时那个清贫而警惕的自己,那时他手中握着的是实打实的兵权和希望。
而如今,尽管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名头,但却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人在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死亡,甚至有些人是意识不到,生命是会消失的,人是会死的,所以他每天都在追求名利,追求财富,追求物质世界的满足。
就比如石敬瑭,年轻的时候为了做皇帝,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可是,现在他要死了,并且还是以皇帝的身份死去,可他并不觉得开心,也不觉得这个九五之尊的身份有什么了。
皇帝的名头,皇帝的身份,既不能驱散死亡的阴影,也无法填补他内心那巨大的,名为“自我”的窟窿。
这一辈子,他就这么活,也要这么死了。
他像所有被欲望驱使的人一样,以为时间无穷,以为死亡遥远,以为只要奋力攫取,就能在永恒的权力盛宴中占得一席之地,直到此刻,当生命的沙漏无可挽回的走向尽头,他才意识到,原来死亡从未走远,它一直平等的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他耗尽一生心血,甚至可以说是付出灵魂的代价换来的这一切,在死亡面前,瞬间失去了所有的重量和价值。
黄金可以贿赂契丹人,但是不能贿赂阎王,玉玺可以号令天下,却无法号令(黑白)无常。
你还是石敬瑭,却已不再是河东的石郎...
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后唐·末帝纪下》
《新五代史·卷八·晋本纪第八》
罗亮.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
夏庆宇.“儿皇帝”石敬瑭历史形象的再认识.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