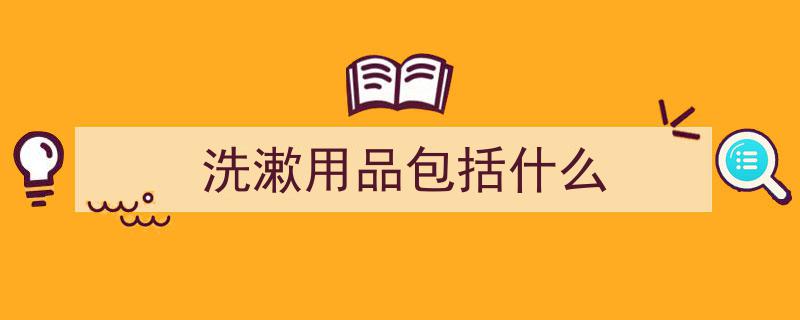古人讲卫生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古时候没有自来水管道,更没有现成的热水器,靠什么?就靠天上落水,脚下好河。江南水多,洗澡尤其方便,有人天天泡水里,河沟里喊一声就下去了。用不着思量太多,水往身上一泼,光着膀子,甩几下胳膊,那叫一个舒坦。夏天晚上村里小孩扎堆洗澡,拎着皂角,劈啪一阵闹,老邻居隔着河还能唠家常。反正水多,人也精细,洗澡当社交,这很江南。可有意思的是,有地方讲究“洗净一身汗”,有地方一年都不见水,难不成他们就不讲卫生了?

西北不一样了。天干水贵,碰上旱年,喝水都费劲,洗澡更难,能省就省。有些地方头发长一年才洗两回——听起来吃惊,实际只是惜水如金。老杨家住在甘肃,家里八口人,一盆水轮流用,洗脸先用,洗澡留到最后。实在没水怎么办?用沙、用灰,用布蘸点油擦一擦,推推搓搓,这也算一种洗法。倒不是没人讲究,真的是没得选。节日、婚丧之事,提前一周筹水,生怕不够分。这时候就见着村头水井排队,有人急,有人私下偷打水。说到卫生,谁不想干净?只是条件拦着,干净只能求其次。
南方沿海倒是牛得很。海边长大的孩子,见惯风大浪急,水资源不叫事。晚上下班,大人带着孩子去河口洗澡,顺便聊聊新鲜事。澡堂子也多,开在河边,冬天门口冒热气,进去一看浴盆排着队。有人洗澡,有人卖香皂,还有人专门捶背。澡堂里啥人都有,隔壁住户争吵,澡堂就是议事厅。有时候一句小道消息,从澡盆边传出来,第二天传遍全城。洗澡这事,在这里,更像一套社交流程,见面点头哈腰,顺手递一块皂角。这东西,在江南水乡简直是标配。

北方不同。北风往脖子里钻,谁还敢三天两头洗沐?头发一浸湿,十天半月不干,生怕染上一身风寒。有钱人家烧热水,大铜盆一端,浓蒸气冲满院。虽说热水足,可普通人家舍不得烧柴。聪明人用热石头烫水,再用草药熬汤,桂枝、艾叶、藿香,有时候就为一身清香。有人说,北方人不爱干净?话不能这样讲。家里的老人常说,“冷水洗头发,热风染肺腑”。一有风寒,洗澡改用熏蒸。越冷越在意细节,北方人也用自己的方法把“洗”这件事做得精致。
有些地方才有点奇怪。比如有人逢年过节才洗一次,原因其实也好猜。一方面是水少,一方面觉得大事大吉,身体要干净。可也不是谁都等得及。年轻人往往偷着在夜里河边洗一回,不敢被老邻居看到,觉得亏待了传统。一个地方一套规矩,谁对谁错,很难分个明白。

历史上有澡堂的不止中国,罗马人更夸张。白天办事,晚上就往公共澡堂跑,男人女人分别有专馆。洗澡时议政、谈生意,政治八卦一锅端,甚至有人带书进去读。澡堂成了资讯枢纽,混混和官员都能碰上面,报警的、拆台的、谈情的都不少。古罗马的澡堂大得离谱,有人统计,鼎盛时期罗马城有900多个“可容千人”的大澡堂。今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盛况?
说回中国,唐代是最讲究洗澡的年代。长安澡堂四处开花,贵族平民都能去。设施讲究:搓背、泡池、按摩。技艺高超的浴童专给达官服务。一场大澡,水温要合宜,香料、药材一样不少。连上元夜洗澡都会配诗吟咏,连气氛都诗意。澡堂还牵出无数人间故事——小贩、算命、媒婆、游客,有人借澡结交,也有人借澡生财。文化层面说,澡堂其实是唐代都市生活的标配,是社交的“流动驿站”。

你要说这些社会细节是大背景,其实具体到个人,全都落在怎么“洗”上。化学制品尚未普及,家家户户都靠天然物什。比如皂角,古人用它不只是因为环保,主要是能起泡,泡多还去油。有人家自种皂荚,一年收割磨粉,用手搓揉出来的沫子,洗完手脚滑溜溜。皂角洗衣,孩子们觉得是个乐子。得,不知怎么误传的,说皂角泡水能治百病,老人们嘱咐孙子多搓两遍,实则是讲究个“去腐生新”。
糠麦汤又是一绝。磨面的糠皮和麦麸煮出来的汤水,温热滑腻。涂在身上,不光清洁力不弱,还带点粮食的清香。有女孩特意用糠麦汤洗头,说发丝更亮。这种土办法,讲的是温和保养,比市面上的化学药水靠谱得多。夏天用着清爽,冬天搓出来打圈圈,热乎乎的,那一刻,人和土地的关系变得更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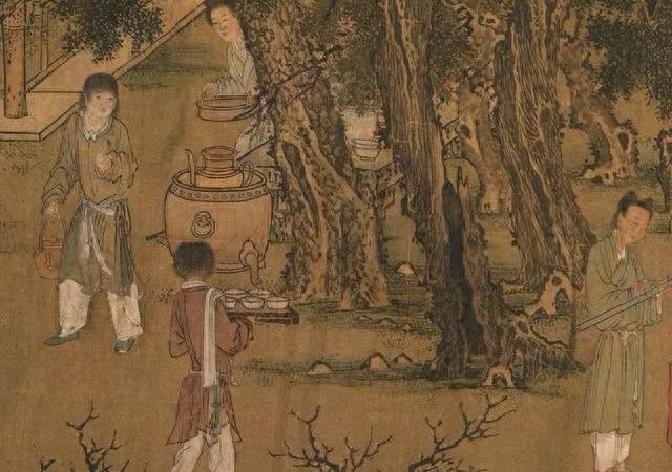
草木灰也不少见。农村柴火锅一开,灶里刨点木灰,加水搅匀,稀稀糊糊。有人直接搓皮肤,也有人拿来漂洗衣裳。老人乐呵呵地说,灰能“吸脏”。草木灰里到底含有碱什么的,没仔细研究,不过据说这玩意也消毒,伤口抹上一点,蚂蚁都不来。传到今天,有些人还用呢?
古时候还讲究加香。薄荷、薰衣草、玫瑰这些草药,院里就种,一掐一把扔水里。夏天薄荷驱蚊,冬天玫瑰暖身。有人说,这些植物精油能治皮肤病,是真是假?没见谁证实过。只是洗完了满身香气,大街上撞见美人回头也不稀奇。家里老人还特意在洗头水里加金银花,信不信随你。

有时说古人比今人差,实在不公。精油提炼、香药煎熬、皂角种植,哪个不是门手艺。有达人会自己做浴泥,茶树油、蜂蜡、薰衣草统统拌上。那种手法,既是清洁也是养生。养生这事古今不同,说不明白到底有多少真讲究。
宗教仪式也和洗澡分不开。恒河沐浴源远流长,印度人至今还信,因此不辞千里赶去“净化”。中国佛门修行,也讲究晨起净体,为的是敬神而顺己心。可不是每个人都迷信宗教,更多人洗澡是疗愈日子里的疲劳,顺带图个热闹自在。
洗澡用具五花八门。竹片搓背、丝瓜络洗脸、铜盆熏身,按理说原始,却耐用。小镇集市偶有卖家现扎丝瓜络,一条街飘柚子香。过了几年,塑料替代了竹片,也少了原来的野趣。传统器皿曾是代代相传的“必需品”,生活哪有一成不变?
有时讲,洗澡频率真那么讲究吗?其实每家每户标准不同。夏天江南一日三洗,有人乐此不疲。北地老宅冬天猫半月不动,没人说不卫生,只说“别惹风”。季节都决定了洗浴节奏,薄荷金银花凉爽,橄榄蜂蜡滋润——谁都精明,顺着天时用东西。逻辑想明白,细节却混乱,每个门道都讲究个“舒服”。
只不过,过去许多洗浴习惯,现在渐渐没了。城市水压稳,化学制品多,一块香皂能顶过去三样工具。澡堂减少,洗浴变得安静,没有了老邻居唠闲话、孩子们打水仗。反过来讲,有些原生态洗浴法其实比现在的花哨要好用些,环保、经济,不留化学残留。
不过细究下来,现代人追求快,图个省事,古人的慢工出细活不再流行。也不是谁都喜欢唐代那一套仪式感,偶尔有人怀旧,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方便第一。信息查到2024年,有研究说,用皂角等天然材料不但健康,还降低了某些皮肤问题。
借用互联网数据来说,国内今年天然手工皂消费比去年上升12%,江浙一带复古澡堂被重新翻新,年轻人乐此不疲。澡堂行业回温,老法子悄然复兴,也许兜兜转转,人们又想回到那个小孩下河、大人搓背的年代。
也许古人的洗澡频率跟生活节奏挂钩,既节约水,也照顾身体。这么一看,有时故意少洗一次,是对身体的温柔呵护?也许只是图省事。总之,生活形式千姿百态,各有滋味。办法虽老,却未必落伍,正经适合自己的,才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