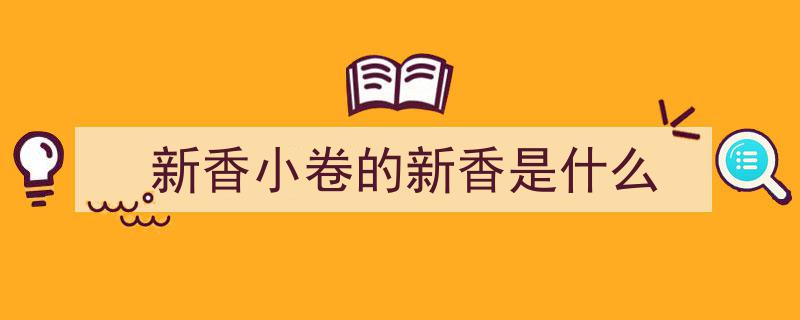“你别来,这几天正公示呢。”
连队传达室那部黑色转盘电话传出的声音,被戈壁的风从线里刮过来,像被砂纸磨了一层边。
我把搪瓷缸从炉子边提下来,缸口磕掉的那圈釉在热气里露出铁色的亮,水里溢出一股熟悉的碱味儿。
五叔把半导体的天线掰直,台子里先是“吱”的一声,随后隐约传来一段颇有精神的播音,字音同样被风削薄,但还是正。
他低头在登记册上签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干脆利落。
我把缸递给他,他接住的手背上有细密的口子,像风在皮肤上刻的小沟。
那年正是八十年代中段,票证还没完全退场,供销社的黑板报上常常写着副食供应和价格,白粉字在风里一抖一抖地干。
我从东北厂区的家属院调来西北实习,单位在营区隔壁的修配厂,风大时两边的广播能互相串音,像两条河在空中交了支流。
五叔在这片戈壁边服役已久,连里都说他手稳心定,修理室里螺丝在他手下像归队的小兵,按粗细排得明明白白。
我到的那天,营门口的白石灰墙粉刷过不久,阳光下有些刺眼,墙上古朴的标语被风磕磕碰碰,边缘起了小卷。
炊事班的烟囱吐出一股淡淡的煤烟味儿,掺着面汤的香,往上盘了一层,旋成一个灰白的圆。
我打小就佩服他那股沉稳劲儿,连说话也不多,话一出口就像被他抻平了,直而不硬。
传达室里有一本厚厚的来电登记,折角处油亮,像被许多手指头反复抹过的旧书页。
电话挂上之前,他沉了一下,声音更低,说“规矩摆在那儿,得稳当”。
我知道他口中的“稳当”不是虚,像他每晚把半导体擦一遍的那股耐心,一回又一回地擦,直擦出细微的亮光。
东北的家那边刚立了春,白杨树皮剥落一层又一层,像旧年从身上退下来,而我这边,风在营院的缝里左拧右拧,总能钻出响动。
奶奶临走前往我包里塞了两双她亲手纳的鞋垫,针脚密密,图案还是她最爱绣的石榴,一看就是盼头儿的样子。

她叮嘱我“帮着看一眼你五叔”,口气温和里有稳妥,我把这句安在心里,像把一块温热的砖放在怀里贴着。
五叔的未婚妻要来探亲的消息就是在这样的风里传到连里的,她从黑龙江那边请了假,托亲戚跑了几趟,领了探亲证,掐着日子坐了硬座。
她寄来的包裹先到了,牛皮纸包上密密匝匝地缠着麻绳,打结处按得很平,揭开是一对枣红的枕套,白滚边像雪沿。
枕套底下压了两小袋炒黄豆和半斤糖,糖纸是绿色的,泛着旧时光的光泽。
我把枕套洗了,晾在营院的铁丝上,风一鼓,枕套咧开笑,像有个安静的人在远处打量这院子。
那几天连里进入提干公示,骨干轮换,规矩自然更紧,走动有登记,晚点名多一遍,修理室的门口多挂了一盏小灯,黄豆粒似的暖光落在扳手的柄上。
我倒也不忧心,知道这类事里头先讲章法,再讲人情,章法稳住,人情才有余地,反之就乱。
夜里风更紧的时候,营区的铁旗杆会“咣当”响两下,随后归于幽静,像在提醒人,许多事要往心里去,不要往嗓子眼儿去。
招待所那边我提前去看了,走廊窄,墙面刷着石灰,半腰贴了花纸,玻璃窗上有薄薄的霜花,像不肯退场的冬。
管理员阿姨戴着一顶灰呢帽,翻账本时用手指扣着页角,指甲上留着洗衣粉泡手的痕。
我把来人姓名、车次、探亲证复印件交上去,阿姨拿铅笔在登记者里划了两道,抬头说了句“安排妥妥的”,语气利落。
我心里就定了三分,回营前顺带去供销社买了两块枣糕和一小包红糖,红糖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团散不开的温热。
这边风沙大,水也是硬的,开水壶里一圈圈白垢像细鳞片,我换水时小心擦,擦不掉的就留着,看多了也就像乡里人脸上的风纹,真。
半导体里偶尔能听到评书先生的嗓子,拉得长长,像胡同口拉糖稀,风小一点时,就能凑成一句整话。

她的火车到了那天,天色灰中带亮,站台上人不多,每个人脸上都像粘了一层旅途的尘。
列车慢慢靠进,车窗里贴着报纸的格子花在晨光里清楚起来,偶尔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呼出的雾弥了一朵又一朵。
她背着军绿色帆布包,包带上绣了她名字的拼音,针脚认认真真,有一两处拐了弯,像手的犹疑。
她鞋跟粘着碎雪,踏上戈壁边的小站,雪响一声又没了,风把那点潮吹干,留下一圈浅浅的印。
她看见我,笑得温稳,眼神一明一暗,像先把心里的话在眼里掂了掂,再端出来。
她说“辛苦你跑一趟”,我说“应该的”,话就平平地落下,稳稳当当。
她又轻声说了一句“甭客气”,东北味儿软软的,把远路缩短了半截,像把马尾辫往前拢了一下,挡住风。
我们一路往招待所走,供销社门口排了队,孩子们趴在玻璃上看油炸糕,眼珠子往里滚,耳朵却被风吹得红。
她只看了一眼,把帆布包往肩上一抬,脚步没停,我心里懂她的节省,也懂她把一份盼头儿省给了后边的日子。
招待所的房间背阳,却干净,床单洗得很实在,有一股晒过的味道,窗台上放着一只蓝边白底的搪瓷缸,盖子合得严。
她把帆布包一件件摊开来,叠好的线衣不带褶,最底下压着一小包黑土,土并不多,包在旧报纸里,外层还套了一个蓝布袋。
她把那包土托着递给我,声音比风小一寸,说“从她家门口刮来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奶奶,从语气里出来的温顺就是。
她说“让他闻闻味儿,想家的时候捏一捏”,嗓音朴实,我却听见了家的影子在风里走了一趟又折回来。
她又掏出一个新搪瓷缸,是白底蓝沿的,盖子周正,内壁洁净,瓷釉光里有个小小的光点,像她的心事。
那天傍晚我回营,风在营门口打转,灰尘往上蒸了一层软,脚印落进去很浅。
五叔在修理室里把腰带从挂钩上拿下来,拉一拉又放回,像预备又像克制,台子上的半导体换到新闻,那头说话的人声沉稳,风里也能听出节拍。

他看了一眼表,指针刚越过一条细线,他顿了一下,像在看一扇门的门缝。
我把招待所的情况说了一遍,他点头,脸上那道纹浅了一点,像沙上的风痕被一泡水抹柔了。
我把新搪瓷缸和那包黑土放在桌角,他用指腹在缸沿上抚过,像摸一只孩子的额头,力道不重,却有心。
夜里临检,修理室门外的灯亮到更深的夜,光沿着门缝流一条细细的线,像耐心落地成形。
第二天午后我端着一碗热面去招待所,面是阳春面,汤清,香油浮着一层薄薄的亮,面条顺着筷子冒起白气,像一扯就能扯出暖意。
她接过碗时先问“他忙不忙”,我说“抽不开身”,她点点头,眼皮底下那道光往里收了一寸,像把心事收进衣襟,别紧。
她又说“他忙就忙呗,别操心我”,这句东北味儿一出来,像一盏小灯在风口安了一把,稳。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窗纸被风轻轻吹鼓又贴回去,像心脏呼吸一样收放,我忽然觉得什么都合适。
晚点名前,营里临时加了一道隐约的规矩,凡事出入要支撑得住问话,问到哪一层,答到哪一层,大家心里有杆秤。
那晚的风把旗杆敲出两声脆响,后勤处的水管冻了头,我和炊事班的人去敲冰,冰层薄,灯光里透出一点青。
回到修理室,五叔把半导体的音量拧小,评书先生的嗓子“咳”了一声,像屋子里有个老人提醒大家歇歇再说。
他开口说“顺延”,语气平稳,像把一只碗从高处挪到低处,不响,不碎。
我心里先是空了一下,又沉稳下来,空的是先前那点理想化,沉的是这句话背后的人心。
他说“规矩归规矩,人心归人心”,他把“归”字放得很准,像扳手卡在了恰好的齿上。
我回招待所把话带到,她只“嗯”了一声,没多问,手边的针线仍一针一针地往前走,针尖在灯下亮一下又收回来。

我心里知道,这“嗯”比许多的话有分量,像一捧温水里没有波,但能顺顺地灌到胃里去。
之后几天,她尽量不在营区周边多走动,招待所和供销社之间的那条路她走得很轻,像有人把脚步的重量替她分了一半。
我看她把带来的红绳挑出来,沿着枕套边又加了一道压线,针脚密得像细雨,落在布上不出声,却把一圈边巩得更牢。
风停一会儿就起一会儿,阳光在营院里洒下来的角度也有轻微的偏移,一天的变化不显,许多天叠起来看,就成了季节的逻辑。
供销社黑板报有一栏写“票证逐步减少,副食供应增加”,字写得端坐,下面一行粉笔道出了新到的白砂糖和豆油数量。
修配厂里老师傅把铸铁件放在炉边烘,铁面冒出一点汗,我从旁拿布擦,布在铁上一蹭就发黑,师傅说“活儿就这么个理儿,慢了急不得”,我听了点头。
未婚妻的假期只有几天,时间在她的额头上没刻出焦虑,而是在她手上积累成了耐心,每一针都像在给时间缝边,不叫它散。
她临走那天,风有点收敛,早晨的阳光像给窗帘搭了肩,把布上的花纹照清楚了。
她把帆布包收拾好,枕套留下,黑土留下,新搪瓷缸也留下,她的东西只带走了必要的几件,像一个人把心房整理出空地留给未来的家具。
她没让五叔送,怕他为难,也怕惹眼,我在站台陪她等车,车还没到,身边隔座的老人掏出一个小铜壶灌水,咕咚两口,坐直了腰。
她看着轨道,眼睛里没哀怨,只有一种往前走的意志,像把身后的门轻轻掩上,意不在关门,而在不惊动屋里的人。
她说“等他闲了我再来”,又把话轻轻压低,补了一句“别给他添乱”,这句北方味儿平平却稳,像一枚小铜扣扣在衣裳的关键处。
火车进站,铁皮在太阳下亮了一下,风把广播里的字刮散了一点,还是能听清列车的次序,她背上包,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定。

车走了,轨道留下震动,像一根看不见的弦从脚底托上来,颤了两下又安静。
我回营的时候,半导体里正播青年合唱,旋律明快,却不张扬,像一队年轻人从风里走出去又走回来。
五叔把新搪瓷缸从桌角端到手上,趁热喝了一口,眉毛在气里冒出一点潮,他把缸沿擦了擦,动作轻,像在抚一件珍物。
那包黑土他也拿在掌心,手一松,土在掌纹里散开一点儿,他把手合上,又捏成一块,说“味儿到位”,我知道他不是只说土味儿。
生活没有被那次“顺延”搅浑,反而像被河里的石头自然改了一点流速,水面更平,底下的流更稳。
我在修配厂的活路一天比一天顺手,拴工牌的红绳磨得发亮,午饭前我常跑一趟供销社,买两串冰糖葫芦给门口的孩子,孩子嘴上一圈红,笑得愿意。
营里偶尔组织义务劳动,大家把仓库后的小渠清出来,渠底的泥翻出来晒一晒,第二天就干成了一层薄薄的皮,踩上去响。
秋天来的时候,风不急不缓,阳光从西边斜下,连队旁的沙丘上长出一点点草,色浅,却是扎得住的东西。
广播里传出一些关乎精简整饬的消息,营区里的讨论不多,话都压在手上的活里,谁手里的活有没有出毛病,一目了然,心里就有数。
这样的日子里,时间变得不像时间,而像一条不显山不露水的线,从每个人的缝隙里穿过去,给衣裳收了边。
第二年春上,连里的评审又提上日程,公示的板子立在修理室门外,名字被粉笔写得端端正正,尾巴轻轻一挑,像对未来示意。
我去招待所看过那只新搪瓷缸,它被她擦得发亮,盖子开开合合不出声,像一口自己的井,水静而深。
半导体还在,背板用棉线扎着,天线掰直后能多收到一两个台,偶尔有远处的歌飘进来,歌声里有清澈的分寸。
评审那天,天气出奇的稳,风像被按住了脚,太阳在营院的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亮,连队的号声听上去也更净。

他出门前把旧搪瓷缸从柜子里拿出来擦擦,又把新缸端出来看一眼,两个缸一新一旧,在灯下反光不同,却都稳。
他把半导体的音量调得极小,像给自己留一条回来的路,又像给屋里的静留一口气。
他走到门口回头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的澄明,像夜里灯下水杯的一圈弧光,薄而亮。
那一天过去,天色沉下来了又亮了一遍,他回来时脸上没刻意的喜,也没有看得见的疲,像一个人把一段路走完,回头看一眼,点点头。
他说“过了”,语气像在宣布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心里的那口气自然也顺了窝。
我把窗户半开着,风从屋里出去再进来,像来回把屋里打量一遍,觉得安然又退下去。
没多久,她的电报也到了,纸薄薄,字不多,句子短,像日常话里的节气,捏在手里就暖。
电报说“忙完我来”,又写“喝水别忘”,这两个“来”与“别忘”,落在眼里就像落在生活里的两个钉,钉得稳。
夏天婚事操办得简朴,院子里搭两张桌子,桌布蓝白格儿,饭碗不够邻居添了几只,热闹有节制,像俭朴里的欢喜,被放在合适的位置。
她穿了一身素色的衣裳,把头发盘得细致,不天天笑的人那天也笑了,笑是从眼睛里往外漫的,不刺激,却润。
五叔把新搪瓷缸递给她,她接住,杯沿碰了一下,叮,很轻,却把两个人的节奏对齐了。
桌上有一台半导体,评书先生还在,嗓子像一条老河流,声音低,曲折处有理路,人声里没有高抬,不用大声,意思早到了。
婚后不久,连里分了一间小房,墙皮有细小的裂,窗框有点走形,阳光从变形的缝往里钻,落在桌上,正好照着半导体和那两只搪瓷缸。
她用一条旧布把窗框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又用线把窗帘下摆折短一些,阳光就收束在桌面的一个方寸里,稳稳地亮。
我去看他们,常把水桶提满,把炉火添稳,把煤渣筛一筛,生活里这些小处,不响,却实打实地把日子垫实了。

她给我盛一碗面,笑着说“先垫垫肚子”,东北话一出来,饭就香了一半,只要有人笑,面就好吃。
五叔在修理室里还是那副样子,扳手摆在应有的位置,螺丝盒有浅有深,标签写得清楚,笔划干净。
半导体偶尔一“吱”,像提醒大家句号到了,别把逗号当句号,这样的声音多听几次,心里也有学问。
有天傍晚风停了,窗帘也停了,空气里有一种难得的安宁,像一个人把鞋脱了,光脚踏在木地板上,脚心里的热气往上走。
他把旧搪瓷缸举起来,在灯下翻一翻,缸底有一块老补钉,圆圆的,边缘磨光了,像时间在它身上坐过,又站起。
他说“有些东西,旧了也好”,我点头,这句话放在搪瓷缸上合适,放在日子上更合适,旧的东西有旧的耐心,新的东西有新的亮光,两者并排,就是完整。
后来我离开西北,回了东北,又沿着河流往南去,去过几个城市,街道有不同的声色,脚下的砖不再是同一块,但我心里一直有两只缸的位置。
每年回去,我都要去看他们,他们不多说,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从来没被风吹走过。
她总要问我“冷不冷”,问完把新搪瓷缸递过来,水温刚好,杯沿干净,瓷釉里映出我的脸,像映出一个不再着急的自己。
半导体的背板棉线换过几次,天线也换过一次,声音更轻,像把故事讲给懂的人听,懂的人听一半,就知道另一半的意思。
我时常会想起那年“顺延”的那些天,风里有一点冷,心里却开始生起小小的热,那热不是火,是一层明亮又不刺眼的光,给人看路。
我也想过如果当时她没来,或者他硬要去送,许多事情或许会有别的模样,可再想想,日子一旦有了“稳当”两字,多半都能走回该走的道。
奶奶后来把当年的鞋垫拿出来给她看,说“你看针脚”,她笑,说“真匀”,两个人的手都曾在布上走过,一老一少的耐心在一块布上握了个手。

她回东北探亲路过我们小城的时候,给我捎了两块黑面饼,外皮烤得微焦,一口咬下去有麦子的新香,我知道那是北方的风味的正经。
我在别处碰到风,就会想起戈壁边的风,那风有劲道,却被人过得稳当,人稳,风也就稳了。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看见一个女孩背着军绿色帆布包,包带上也绣了字,针脚歪了一点,我笑了,心里涌起一种熟悉的亲近。
列车广播里播出青年合唱,歌声平和,我想到半导体里的歌,还有那两只搪瓷缸的光,像两个小太阳,照顾着一方桌面,桌面上有饭,有手,有平常话。
我知道五叔后来还接连带了几批新兵,他教他们分螺丝,教他们拧螺丝,教他们手上心里都得稳,他用的不是道理,是动作和眼神,人家就懂了。
他有时也自个儿笑,说“哎呀妈呀,老手艺”,这句带点儿方言的自嘲,不重,却轻轻点在生活的脉上。
她在他们的小屋里干干净净地布置,墙角摆一盆吊兰,叶子从架上垂下来,绿色柔软,夏天的时候风一来,叶尖轻轻点着墙面,像轻轻点头。
他们的孩子从学前班到小学,字一撇一捺慢慢写稳了,家里贴一张小人的画,小人笑得大,画角用胶水贴得服帖。
有一年冬天我去,他们围在小炉子边烤红薯,红薯皮裂一条缝,糖水往外冒,屋里甜,人也甜。
他把旧搪瓷缸递给我,我捧着,缸底的补钉把温度牢牢攥住,手心里热,我忽然觉得那一小块补钉像一块信心,旧得耐用。
窗外的风绕过屋角,没有在窗纸上留出太重的痕,窗台上的黑土被她换了个新包,依然压在半导体旁边,有时候她会解开闻一闻,然后笑,说“这味儿在呢”。
我点头,心里觉得,这味儿就是家常,就是人心里的方向,不必抬头看星,闻一下,就知道往哪儿走。

很多年过去了,营院翻修了几回,墙上的白灰更净,路面从土到砂石再到水泥,鞋底踩上去的声音变了,但院子里的安分没变。
修理室换了新灯,亮而不刺,扳手和螺丝换了一批又一批,旧盒子被她擦干净,依旧作为盒子,装别的,也装得稳。
我走的时候,半导体“吱”了一声,像一个老朋友咳了一声,我回头看,五叔把它的天线轻轻按下又轻轻抬起,像摸一只小猫的背,手法轻柔。
门外天光正好,风像把自己放慢了一秒,沙尘也收了性子,阳光落在两只搪瓷缸上,缸面上两团小小的亮安安静静,像两个内心有火的人,不烧不烫,却一直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