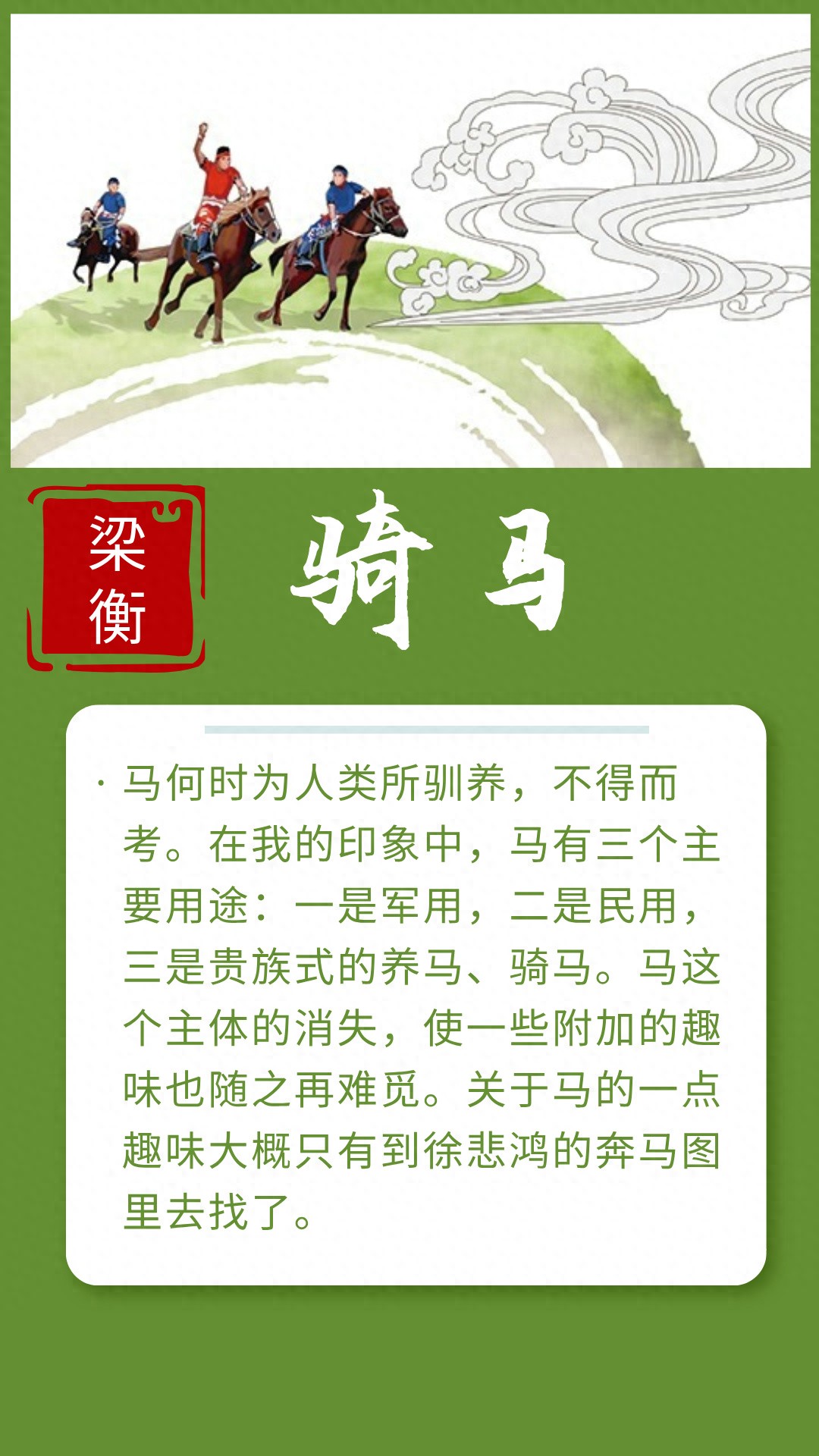
我与马最亲密的一段接触是在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的一年。
内蒙古河套,是个半农半牧,又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村除种地用马,又多养了一些马,所以不像中原农区对马管得那样严格,干活时牵之于地,收工后系之于槽。这里的马相当自由,大部分是不干活的游走之徒。少量干活的也是一收工就摘掉笼头脱缰而去。于是常有大量的散马在村外的沙滩上或收割过的庄稼地里幸福地撒欢、嘶鸣,有一口没一口地伸长脖颈吃着地上青草。也有放马人,一般是派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子去管这些马。说是放马,其实是伴这些马玩。
来村落户一年,我已经与村民混得很熟了。一天,马倌小李子突然问我们敢不敢骑马,“敢!”我们七八个男女生齐声答道,并踊跃地举手,要求给一匹马。马的骑法有两种:一是骑鞍马,就是整齐地备上鞍子,套好笼头,手握缰绳,双足踩蹬,这是正规骑法。还有一种野路子,就是什么也不要,人骑马上,手抓马鬃,乘风而去。一般放马的人特别是男孩子惯用此法,俗称骑光背马,当地人叫骑“产马”。这个字该怎么写,没有人去考证。村子里就是这样,很多字只鲜活在口头上,遇到非要写的时候,就胡乱填上一个同音字。比如当地产一种芨芨草,这是学名,而大队、公社的文书中都写成“只及草”,而且还创造性地在“只及”二字上又各加了一个草头。这个“产马”的“产”直到多年后我才在一本旧字典里查到,应写作“骣”,也是这个音,释义为:骑马不加鞍辔。就是骑光背马。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么一个偏僻的方言竟上接千载,直通古文,有一种深山藏古寺的意境。
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一匹马。小李子服务周到,女同学就挑最老实的马,找个能踏脚的土墩扶上去。我们随便接过一匹,但也要有人帮忙才能骑上去。你想第一次骑马,马背圆滚又无鞍辔缰绳可抓,马一跑开人就翻了下来。好在都是沙地,也摔不痛。就是马跑的过程中,你实在抓不住了,也可主动滚落下来,不会有事的。小时候在村里就听人说,老马识途,护主佑人,不像毛驴那么奸滑,“毛驴是个鬼,摔人不断胳膊就断腿”。那天,大家玩兴很浓,跌下又爬上,学而不厌。
等到你基本上能驾驭马让它开走时,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马走慢步,或碎步,四个蹄子前后交错地踏行。步子走得好的马被称为“走马”,人坐其上稳如坐轿。二是马慢跑,直至飞奔起来。当地的孩子称之为“抹奔子”。这也是一个极形象又专业的方言。“奔子”好理解,奔腾之意,妙在这个“抹”字上。因为马奔腾起来后,你的双手抓着马鬃或缰绳,像是在顺着马的长脖颈从前往后地来回抹动,十分传神,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立即在脑子里把它写了出来。待我们能初步掌握了马时,小李子和他的伙伴们就大喊:“抹奔子!抹奔子!”,意即让马跑起来,飞起来。这时马就不是四条腿交错着地了,而是像饿虎扑食一样,两前腿齐向前扑出,刚一落地两腿又跟上来点地弹出,波浪式飞跃。这才是骑者最享受的时刻,人如在浪尖上荡滑板,一波接着一波;如雄鹰展翅,上下翻腾。但这里说的是理想状态,是熟练的骑手。作为新手只是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已自惊喜,而且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原来,人的屁股与马背是一对矛盾。你向下压它,它就向上顶你。静止时这矛盾还不明显,马一颠起来,就把人弹了上去;人再落下来,屁股就重重地摔在马背上,就这样来回对撞。而马背是什么?就是一条硬硬的大脊梁骨。李贺写马诗云:“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它硬如铁、窄如刀,就这样一下一下地砍在你的屁股和尾椎骨上,这怎么受得了。所以正规的骑马一定要备鞍子。而骣骑的要领是必须人马一体,就像有什么东西把你和马粘在一起,人即马,马即人,永远是上下一起动。这时二者已不是一对矛盾,而合为矛盾的同一方,共同去对付另一方——大地,或踏地而行,或点地而飞。而这个任务,人就不必管了,交给马去完成,它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你就坐享其乐吧。耳边呼呼秋风过,眼观四野花草香。但这种人马合一的状态要非常纯熟的骑手才能做到,或者如小李子这样从小和马一起玩大的孩子。
那天我们痛痛快快地“抹”了一回“奔子”,可是到了晚上就甜尽苦来,乐极生悲。先是腰和两腿酸痛,因为骑马的时候双腿要用力夹紧马背,腰也前后晃动扭曲。这还是其次,最难堪而又难言的是,屁股连同尾椎骨经马背这把“骨刀”上下地砍剁,晚上退下裤子,已是皮破肉绽,渗出血水,火辣辣地疼。四个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喊爹叫娘。聊着,聊着,大家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忽然觉得我们就是一群“骣马”。人靠衣裳马靠鞍,我们本来以“骣马”之身入学,经过五年的大学教育,毕业时学校都给配了不同“鞍具”:天文、生物、化学、历史、建筑等等。但一出校门就一律被摘鞍除蹬,不分专业,不问对口,来到这黄沙窝子里来与草木共生同乐。于是再不多想,就说:睡觉!睡觉!迷迷糊糊不觉东方之既白。
第二天,我们碍于面子照样出工,只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种难言之痛,大约过了一周才慢慢康复。但我们还是照骑不误,西风骏马本无价,秋风黄沙皆有情,天赐之乐何能放过。而且臀底功从磨砺出,骑马乐从苦中来,之后也就渐渐痛少乐多了。套用李白的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好马骑无人!一年后政策落实,劳动结束,男女同学都分赴各地。
那次骑马之后过了30年,我到四川九寨沟又得了一次骑马的机会。主人是一个下海文人,先做汽车生意,玩腻了钢铁的“宝马”“悍马”,又来做山水旅游,就自己买了一匹有血有肉、红鬃白蹄的真宝马,金辔银鞭,豪华一回。那天他邀我们同登青、甘、川三省之交的一座山头,遥望黄河从天际而来,在茫茫草地上划过它出世以来壮美的第一湾,龙蛇一道,闪烁明灭,顿觉风展衣袖,天地入胸,欲扶摇而去。回程时,主人将他的宝马借我一骑。我踩蹬翻身,一抖缰绳,顺着弯弯的山道直冲而下。耳旁风声呼呼,绿树花草倒退而去,我又找回了当年 “抹奔子”的感觉。
来源:《当代贵州》2024年第12期
海报制作/王永懿
融媒编辑/张蕊
二审/刘跃 郎艳林
三审/吴文仙 梁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