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中期,数十万建设者在井陉大地谱写辉煌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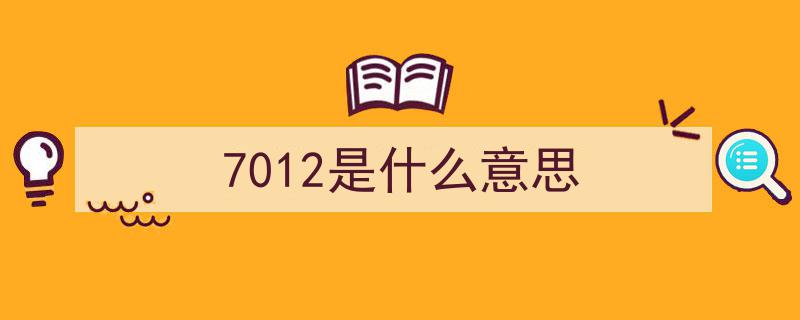
您提到的“古老的井陉大地上,上个世纪中期,曾有数十万建设者涌向了这里”描绘了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和时代记忆的场景。结合中国的历史背景,这很可能指的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了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建设者响应号召,来到井陉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时期。
井陉地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在20世纪中期,井陉地区以其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了国家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特别是井陉矿务局的建设和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建设者。
这些建设者中,有许多是响应国家号召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们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热情,来到井陉这个当时相对落后的地区,克服了种种困难,参与了煤矿、铁路、工厂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为井陉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建设者的故事,是井陉地区乃至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井陉地区建设者故事的信息,可以查阅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文学作品或者纪录片,例如《井陉记忆》、《井陉建设者》等,这些资料可能会为您提供更详细和生动的了解。
相关内容:
要是你曾在石家庄西边混过,一定听过井陉。说起来它可不简单——这地方上过“千年古县”那批名单,听上去就自带一层历史滤镜,再加上那沟沟壑壑的地势,四面环山、里头低洼,远远看着还真有点像一口井,怪不得老祖宗就这么叫了。这里离娘子关也就几十公里,“背水一战”这些大场面都和井陉脱不开关系,光听名字就知道,这地儿过去不是省油的灯。
我小时候隔三差五被爷爷拖过去,说是去瞧“老山沟的骨气”。其实,他嘴里那骨气,换成现在的说法,大概算一种“倔”。井陉真正热闹起来的事,估摸着要从微水发电厂说起。六十多年前整出来的,当年在整个河北都是响当当的单位。七八十年代的小城日子,一到下班点,电厂门口可热闹了。小卖部炊烟一缕和那大喇叭广播混一块儿,围着电厂转一圈,谁家啥日子,十里八村的人都摸个门儿清。那时候电厂的孩子也算“圈内人”,我小学就有一半同学是电厂的子弟,穿得好,话多,人还精明,课间打乒乓能一挑三。不说别的,那会儿家里能通上24小时的电,冬天有暖气,就能让周边山村的亲戚羡慕上大半年。
可惜世事难料,“铁饭碗”也不是铁打的。后来国家调整规划,电厂说关就关了,工人一部分往西柏坡去了,还有一队更惨,被发配到了呼伦贝尔,说白了就是再也没回来。电厂的大门自此斑驳掉漆,操场上荒起了草。留下来的,只剩下大孩子一拧眉头就骂两句,“还不如上山放羊自在。”这些场面,外人其实很难体会那种失落。
说到井陉,你还得绕不开那些名字听着神秘兮兮的工厂。五六十年代,这儿悄悄地多出了些“带编号”的军工厂。3502厂和3514厂——你在路边问一声“401”和“402”,八成有人跟你反应过来。工人当年响应上面号召,从北京、天津甚至东北一路迁过来,许多是带着家眷的。一到井陉,才发现这儿天真冷,屋子里潮气直往被窝里钻。头几年啥都得自己动手,房子一砖一瓦盖出来,连做饭都要跑砖瓦窑催活。你说他们苦,那是苦,但要说没乐子?也不见得。平房前栽树、院子里喂鸡,下班还能凑三五同事侃一天的家常,逢年过节一支口琴谁都能唱两嗓子。许多人起初根本没想会在这儿扎根,结果一住二十年,白发生出来了。
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军厂说搬就搬,人一下就分流到省城,井陉似乎静了好些年。我还记得有位阿姨,坐在家属楼边上剥玉米,讲她年轻时在铸造车间拎着小铁桶,每天要查个几十个阀门,那汗水味儿和如今写字楼里的空调气息,谁都不假装愿意替换。过去她觉得山沟子显得寂寞,搬出来以后,许多夜里还梦回那一段工厂时光。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叫五四二工程,代号7012。这名字听着就像什么秘密任务,实际那会儿“秀林镇”一带变成了半个新城区,各地的能工巧匠都往山里钻。20厂、50厂、60厂、70厂外加个制砖厂,长长的都是流水线。那些年,要是在南障城路口放鞭炮,北障城都能听见。有小饭馆专门给工人送饭,老板娘一天提着两壶热豆浆满镇跑,累得直不起腰。只可惜,风头劲了没几年,工厂陆陆续续外迁,有的干脆倒闭,厂区变烂尾,白天有人捡砖头,晚上猫狗成群。人来人往,留下空空的工棚。老井陉人说,没了工厂的城镇,也没了那种“人扎堆、脸贴脸、你我都有用武之地”的热闹。
其实,那些年井陉的厂矿数不过来:不光有铝厂、玻璃厂,有家叫河北印染机械的,坊间传一台老机器开满马力能震得整个街区发抖。不单是民用的,还有部队仓库、医药库。最夸张的一年,邻近几村的小青年都爱往县城跑,哪怕只是为了拎一袋便宜面粉或看一眼穿制服的伐子哥。你说热闹也好,说未来可期也罢,眼下都只剩回忆了。如今还在井陉扛住不走的工厂,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天气转暖,老电厂家属楼的老人们就会搬个板凳,在旧花坛边唠嗑。有一回,一个老头说,“这地方啊,给过咱光景,也给过咱寂寞,只是人不能都像机器,一关电闸啥痕迹都不留。”这话我那时没全懂,现在回头想,或许真有点意思。
再回井陉,路宽了,楼高了,从省会开车来半小时都到,县城里新开了不少咖啡馆。听说石家庄人周末爱往这边跑,说空气好、山水美。可转角的老厂宿舍,外墙脱落,孩子们在晒衣绳下奔跑,大人们仿佛还守着一段未完待续的故事。时间过去了,模样是真的变了,但一回头,那些曾在这里点灯熬油、苦乐自知的人事,却像山里的风,始终吹不散。
有时候我忍不住想:这些和井陉一起老去的爷爷奶奶,他们会不会半夜还梦回青年时的热闹?老伙计们还在车间搭胳膊说笑,饭香混着机油味。也许下次路过井陉,不妨多走几步,抬头看看山,看那些房子和巷子。说不定在某个转角,还能瞧见当年意气风发的影子,正借着微水坝的风穿街而行,走向下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