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这盘大棋,光说说话这一点就够复杂了。你要在东北喝酒,隔壁大哥一句“杠杠的”让南方人脑袋一懵;转身去了四川,茶馆一坐,“雄起”“咋个”夹杂在烟雾缭绕里,听不懂都不好意思叫自己中国人。其实吧,别说省份,就算一县之隔,说话都能天差地别。小时候我家北方亲戚来这边,我奶奶还得专门“翻译”,怕客人吃亏。要不是这些年国家发力推广普通话,谁敢说自己能和全国各地的人一句话不带障碍地对话呢?

普通话这事,其实跟咱们历史上的不少纷争有点像。一开始玩儿的是“官话”,说白了就是权力顶层的人怎么说,大家只能跟着凑合。你听过新疆某地的小学老师,硬着头皮教普通话,自己腔调却像唱“花儿”?还真是有的。这种“标准音”不是天生的,是一代代移风易俗硬捏出来的。说到这里,不少北方人都以为,哎呀,北京不就是普通话发源地嘛?其实你要真去河北承德滦平县问问就知道,那里才是“普通话之乡”。但这有多巧?滦平的口音本来就偏向标准普通话,不夹杂奇奇怪怪的儿化音,也没南方那种绕嘴的韵脚,听着干脆。
关于滦平普通话的地道,咱们不必光看地图,更得琢磨背后的人事变迁。清朝定都北京嘛,本该带火北京话。可北京话,“儿儿”满天飞,讲究起来对南方人一点也不友好。倒是滦平那一带,早年间往来多是北上闯荡的书生与官吏,本地口音逐渐规整,慢慢被当成朝廷里“上话”的标准。后来的语言委员会设立标准时,也会拉上滦平老乡让他们说两句,听听那韵味是不是能“服众”。说普通话就像吃饺子,你得皮薄馅多才顺口。滦平县的人会一脸自信拍拍胸脯,“咱这话,播音员都得来学!”有时候遇见外地小年轻来寻“原声”,当地大爷笑着一桌麻将还教人怎么“咬准儿”,说的一口顺溜,弄得人家都要录音回去慢慢琢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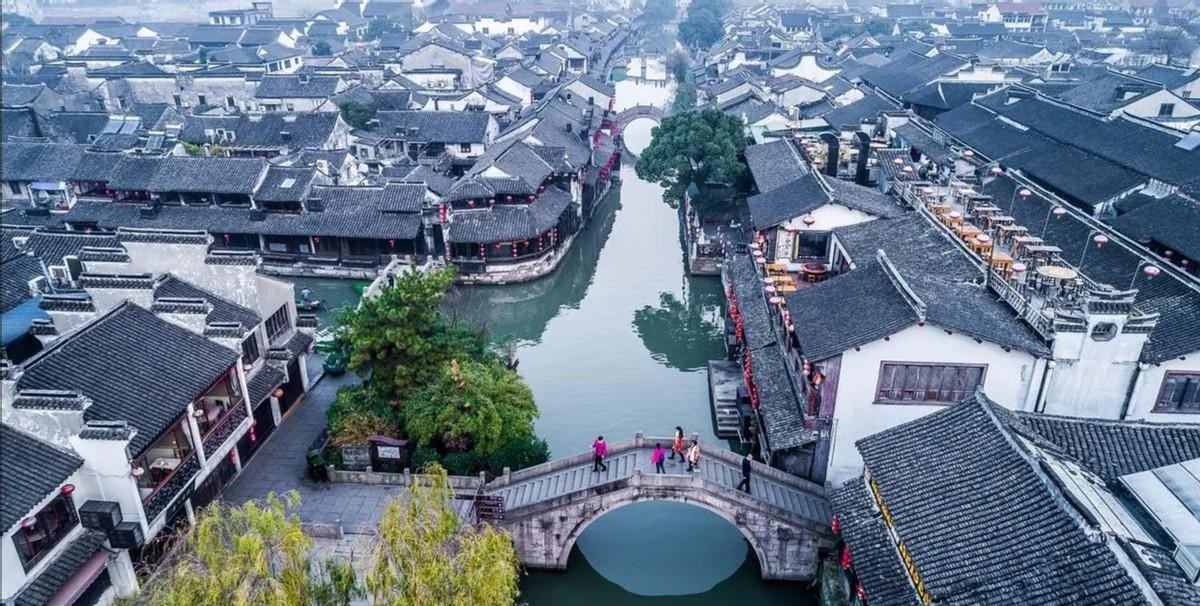
再说北京。谁说“首都出标准音”?其实帝都虽然几百年都是权力中心,但“京片子”里的味道有点重。这个不光体现在“儿化音儿”,还在于那种“带劲”——很多外省人一听北京人说话,觉得亲切是亲切,就是有点“拽”。其实这都源于北京城里混杂了各地口音。明清时节,四面八方进京赶考的青年一窝蜂,外地人进北京,当地小吃能把韭菜盒子和炸酱面都捏出新味,语言也是,各种说法“你冲我,我掺你”,一来二去,老北京话就带上了各路调。可再拽也拦不住“官定标准”,一搞推广,儿化音什么的被“下放”成了地方特色——你说“普通话”,但“北京腔”却只能做母本,还得加一层滤镜。
北京话的影响力也不光凭政治。你去琢磨相声,这些年郭德纲、岳云鹏,把北京话说得又地道又流畅。老百姓听惯了,觉得好笑又易懂。文化辐射嘛,比啥都快。还有诗歌、话剧、电视剧,那叫一个广,谁家小孩没试过模仿“北京话”来逗大人乐?北京成了大家学习的范本,也怪不得普通话先在这普及得深。

东三省其实也是狠角色,尤其黑龙江。不少人认为东北人嘴皮子快,说话一整个“带劲”。不过,黑龙江的普通话标准度可是一顶一的。这里的哈市小伙、齐市姑娘说话讲究清楚,什么翘舌、送气,全都琢磨透了。讲个真事儿,大庆石油工人搬家后,孩子上学普通话分分钟拿第一。这一带因为建国后新产业集中,外来人口不断,大家都习惯“说标准话才好混”,普通话越发普及。不少节目主持出生黑龙江,训练出来,转了一圈回来当阿姨舅舅教小孩发音,周围人都说:“你这嘴,播音台上跑不了!”
要说东北的整体普通话水平咋样,你翻到吉林,算是齐齐哈尔旁边那个“大兄弟”。虽说整体很好,但东边那块,少数民族多点,学普通话有点儿“跨界”。像延边那块,朝鲜族小学校里,孩子们先学朝鲜语,再学普通话,两种语音在舌头上打架。长春的戏剧团那些演员,成天互相练习,普通话说得珠圆玉润,听着就干净。文艺宣传是硬件,有了这个,吉林普通话推广可谓“老师带徒弟”,小孩学得专注,大人看了高兴。

东北三兄弟里,辽宁却经常被拿来“开涮”。大连、鞍山还有铁岭,每个地方口音能让隔壁省份人当乐子讲。尤其铁岭,一说就是小品、赵本山,都知道他会“抻腔”,但一进正经场合还得学点儿“标准话”。沈阳的年轻人常爱跟本地话掺普通话,尾音一翘,感觉像打小带点儿舞台气。其实整个辽宁就朝阳那块稍微接近普通话,但鼻音又重,标准度还是差点意思。
内蒙古普通话标准度高,这事儿要讲讲当年“闯关东”。不少人有爷爷奶奶是从山东、河北移过来的,口音一开始带南方味。可是东部“闯”过来的人多了,逐渐和东北互通有无,你唱一段“二人台”,曲调都能混进去普通话发音训练。这种语言的深度融合,让内蒙古的普通话有了一层独自的“稳”——既有北方腔的利索,又能压住南方调的碎碎念。如今小学、初中都上普通话课,校门口家长一聊天,说得比谁都正。

南方地区,终于轮到了江苏。这地理位置说来真“讨巧”,夹在南北之间,文化偏北又不彻底“北”,普通话就成了个夹心饼干。南京、苏州的学校里,老师会反复纠正学生发音,要没普通话,考试分数都差点儿。江苏经济发达,早年间推普工程搞得热火朝天,老师家长齐上阵。你看,城里孩子不声不响说普通话,整个班里就感觉像“上海翻译协会”——南腔混北调,最后语言矫正都归普通话。
浙江普通话也说得挺顺,虽没江苏那种“地利”,但优势在于啥?教育和经济一向发达,大伙重视孩子口音修正。“吴侬软语”柔软得像布棉被,但小学老师开口普通话能柔声细语又一板一眼。杭州、宁波的年轻人,约会聊天也不喜欢野地方言,普通话成了“潮流”。前些年,某网络主播口音几乎标准,都说“浙江这地,普通话人才辈出”。

安徽,讲到普通话又新鲜。老一辈人都记得,明朝的时候官话定在南京,其实相当于半个安徽话做底子。到清朝变动,安徽话影响“官舌”的程度还不小,因此安徽孩子学普通话总感觉没障碍。你进合肥、六安的小学,老师上课念课文,和北方大城市没多少区别。顺道一提,有个屯溪的朋友,走遍长江以北还没被纠过吐字,大家都叫他“标准音”。
天津这城市,普通话水平排第十,总让当地人不服气。天津话“儿化音”比北京还浮夸,“十四是十四”那顺口溜经典得百听不烦。小时候,邻居家小孩学普通话,老师拿着录音机让孩子反复比对“是”和“四”,一不小心就变成“十”。不过这些年,老少爷们越来越重视标准发音。你进地铁,听见播报员那声“请扶好”,口音已经没有多少天津味儿。大家都说,再过几年,兴许还能和滦平、北京“掰掰手腕”。

说到家乡,也忍不住想起那些年大街上推普的大喇叭,“大家讲普通话,沟通你我他”。现在呢,不少地方孩子说话跟央视播音只差一口气。你觉得你的家乡普通话标准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翻车”故事?欢迎唠嗑几句,看看咱们这口普通话,究竟能有几分“本味”——也许,语言这东西,咱们标准了,但生活的滋味和乡音却永远留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