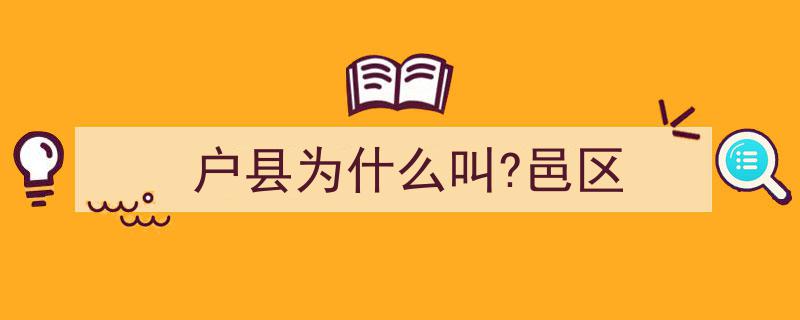鄠邑区·渼陂湖

云识潇湘雨,风知鄠杜秋。
唐会昌元年(841)秋,诗人许浑在《将赴京师蒜山津送客还荆渚》如此描写自己面对离别与季节变换之时的感悟。鄠杜是鄠邑和杜陵(汉宣帝陵)的合称,最早见于东汉班固《西都赋》的记载,因其地理毗邻且同属长安近畿要地而得名。
得益于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以及独特的区位等因素,西安城南、终南山下的这片土地在千百年来曾频繁地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西晋潘安在《西征赋》当中将“林茂有鄠之竹”视为长安风物的代表,南宋诗人廖行之用“力绵何以振,敢意鄠县功”来表达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唐朝·鄠县地图
长安南郊,这里的魅力也体现在曾是十三个王朝的京畿重地,穿越千年之后仍有“关中山水最佳处”之誉。这里曾是有扈氏的都城的所在地,《墨子·尚贤》记载禹在阴方之中举荐伯益为继承人,夏禹逝世后,启最终从伯益手中篡夺了政权,有扈氏败于夏启。后来,伯益的后代嬴非子建立了秦国,秦人在当周平王东迁时护送有功,故将岐丰之地赐予秦襄公,秦人从甘肃秦亭迁入关中故地,之后又将扈地改名为具有纪念和祭祀意义的鄠字。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国迁都咸阳之后设置了鄠县(另说西汉初年置鄠县),县治鄠邑即今鄠邑区北的韩村附近,鄠县作为我国县级区划的身份和地名的历史至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足见其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西汉·鄠县地图
县名由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一是以雩祭得名,雩祭是古代求雨的祭祀活动之一,《周礼》有“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的记载;其二是认为鄠县之名源自秦国的鄠邑,因这里在夏朝为有扈氏国(扈国)而得名扈邑。可见鄠邑作为地名的历史比鄠县更为悠久,更难得的是在此后各代的漫长岁月中,鄠县之名均得以延续,因而成为中国几千年未曾改名的千年古县的代表之一。
隋大业十年(614)鄠县移治今鄠邑区,后来鄠县补齐了改名的这一课。1964年9月10日在全国改革生僻字繁体字地名的情况下,鄠县被改名为户县。鄠县籍杨明轩先生撰写并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指出取扈字上半部分改称户县,既符合历史渊源,又便于书写和认知。

鄠邑区地图
此时距离她最早出现的先秦已过去了2314年,在给大众带来书写和认读等方面的便利之时,也让鄠县这个货真价实的千年古县之名因此消失,而作为地名专用字的鄠字的使用频率则在这次改动后变得更罕见了。
应该说地名的改动是把双刃剑,很难简单判断利弊,更要从符合当地实际、习惯、历史文化传承以及成本等多个角度来综合考量,这种情形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有变化,比如一个县级区划现在改名要比几十年前改名的影响和成本更大,因此地名的改动才值得慎重对待。

虽然鄠县的消失有惋惜之处,但与众多消失就湮没在历史里的古地名相比,鹄书认为鄠县也是幸运的:2016年12月户县获批撤县设区,同时更名为鄠邑区。这次改名仍然有着毁誉参半的风险,鄠这个地名专用字能够回归自然是好的,同时也意味着用52年时间积累起来的户县这个品牌要逐渐被取代,比如户县葡萄、户县软面、户县黄酒等特产需要时间来进行品牌的交替和积累;此外鄠邑这个生僻的词语也让人需要时间适应。
如今户县以鄠邑区的新身份出现也有八年多时间了,外界大多已习惯了鄠邑这个名字,在历史底蕴和天时地利人和等利好因素加持下,鄠邑也逐渐成为与当地匹配的新品牌。那么户县当年为何要改为鄠邑区呢,鄠邑区取代户县的改动成功与否呢?个人觉得户县更名为鄠邑主要是由以下方面原因决定的。

鄠邑·朱雀山
首先是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出现52年的户县相比,鄠字贯穿了当地设县的绝大部分历史,重拾品牌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因此鄠邑虽然比鄠县生僻,但作为鄠县的地名源头,它不仅有更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有能避免户县区这类地名中出现两个通名的情况。
其次是在单字县撤县设区之时,改名很可能成为“刚需”,比如赣州市赣县改为赣县区、梅州市梅县改为梅县区、三明市沙县改为沙县区等范例,因此户县设区之时若没以鄠邑区命名,大概率也会成为西安市鄠县区或户县区。

来源:鄠邑区网信办
康熙字典记载鄠又与扈通,从有扈氏到扈邑、从鄠邑到鄠县、从鄠县到户县,再从鄠县到扈邑;这里的历史底蕴由此可见一斑,其地名的数次演变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
个人觉得户县改为鄠邑区虽然短期内有一些负面影响,假以时日是可以扬长避短的,因此从长远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经历系列的转变之后这里又重拾两千多年前最原始的称呼,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地名意境,对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