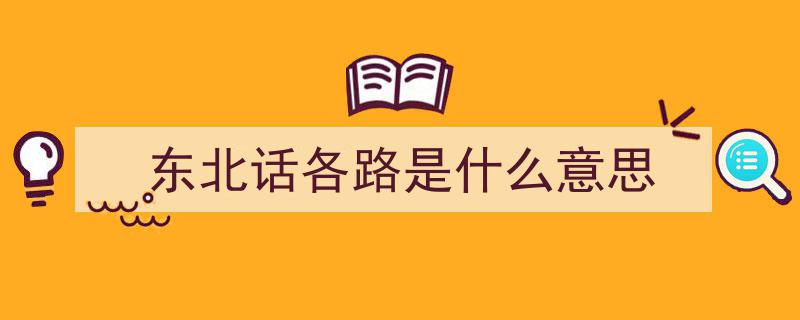长春人常说,人民大街和重庆路口,是这座城的“心眼”。有事没事儿,哪怕乱转一圈,最后多半还得回到这口子歇歇脚。可你信不信?眼下摩登高楼一溜排开的市中心,其实还藏着点老底子:几座拼过风雨的老房子,像顽强的老人一样,寸步不让地留在了城里最热闹的路口。

这是2024年9月29日,傍晚六点,我在重庆路西段溜达的时候随手按下快门——那几块灰白老墙,还站在那里,带着点逞强,也带着点怀旧。每次拍这些老屋,我都有点小情绪。可能因为它们站得太久,经历了太多长春的天亮和入夜,是那种见过世面的坚韧,光用时间打磨不出。
快看,道南那一排,北燕照相馆还挺着胸脯,其它几幢小楼也来凑热闹,像是老友会面,谁都不想先走。照相馆门口挂着的招牌早不见了,楼下那家理发店也干过三茬老板,但有时候傍晚灯泡一亮,路人还是会多看两眼,仿佛能从烟火气里闻出一股老长春味儿。

穿过马路往北走,视觉里就是一串更“讲究”的老建筑。实验饭店、春城剧场还有那幢省交通厅旧楼,都攒在一块儿,说不上奢华,却很经得起端详。交通厅那楼当年可算是豪气冲天,据说白墙青窗,从南到北站得笔直,一进门就是开会的味儿。有那么几年,谁调到这儿上班,家里都觉得出息了。也不怪当年的长春人对这些“西式楼”念念不忘,人家的城也不过两百来年,这点历史印记,铁疙瘩也得护着。
时间刷到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要说最有人气的一带,还得是这片办公楼。那会儿饭店的饭菜刚上新花样,剧场边传来二人转的开腔,街头巷尾满是踩着自行车的上班族。赶上节日,大伙穿得精神,小孩儿攥着糖人贪看橱窗,不知道有多少邻居、亲戚、朋友,都曾在饭店门口约好见面,实在有点生活的小细节。

再跳个年头吧,1993年,这地方正是另一个模样。老照片翻出来看,你能认出当时的“五百”——也就是百货公司第五商店的大楼,那可真是热闹过头。谁家结婚添置家电,过年买新衣,甚至凑巧路过,都要往里钻一钻。老成衣柜外头贴着奖票广告,有的孩子就在外头吵闹,陪着大人等电梯。现在五百已经撤了,楼里新换了招牌,可每次我路过,总还是能想起小时候姥姥牵着我的手在人群里穿梭,满耳朵全是各路东北话的大嗓门。
“北国之春大酒店”也是那时候刚盖起,顶楼玻璃窗子一溜反光,据说一晚上能招待半个吉林省的婚宴。那时建国路、西安桥、重庆路一路电闪雷鸣地新楼开工。工地里灰大、车响,但每一砖一瓦都是城里人盼头。贵重的也许不是建筑本身,是建楼时那种所有人自带野心的劲头儿。

这些年国贸、工行的大厦越盖越高,新时代的标志全都光鲜亮丽——可再怎么高档,也替代不了老房子给人的那点踏实感。老交通厅办公楼的楼道里,墙上还贴着三四十年前的宣传画,有老人晨练完在长椅上晒太阳,偶尔掉头望一眼那些年轻人急匆匆进写字楼,再坐会儿,琢磨着“日子过得真快”。
我记得有一回碰见个修缮工人,在拆掉老剧场一块破玻璃。问他这房子还能撑几年,他犹豫半晌,说:“得修还得修,老大家的东西,拆不容易。”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全涌上来——也许每栋老房子,都挤着过去村镇、家族、饭店、靠山帮的影子,拆一个不光是丢一堵墙,大半段市井日子也跟着没了。

可世界总在换着马甲往前冲。新建的步行街闪耀得像隔世,而在人来人往中,好多外地来长春的年轻人,压根不晓得他们脚下踩着的,就是一寸寸揉进几代人记忆的泥土。楼前老槐树上的鸟窝,也许还和老市长上任那年一样,不知不觉熬过风和雨。我们有时候太着急往前奔,总丢了点啥。
所以我拍这些老房子,或者说,拍下这些过去的痕迹,其实并没期望它们能永远在那儿。而是怕哪天真的走过路口,“北燕照相馆”不见了,“五百”没有了,“交通厅”只剩块牌子,才发现再没法和过去做个照面。人们总说长春年轻,其实这几处老楼正是这座城市的脸——哪怕皱了点、破了点,总比千篇一律的新大楼有层次。
如果哪天你路过人民大街和重庆路交口,不妨慢一点,抬个头,愿意的话,用手机拍一张。这几栋老楼还在,街角烟火气还在,也许,我们依然能认得家一样的城市。谁能说清,下一个十年二十年,这小块地方,是不是还躲得过重建的锤子?是不是还能给人留下一点“活过”的证据?这事啊,谁也保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