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城市改名字的事儿,说起来总带点无奈和好玩。原来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有画面感,改来改去,有的越改越没感觉,有的干脆让人忍不住吐槽:到底是谁拍脑袋定的?你要是常常瞅着地图想事情,有些名字能让人空想半小时,不光是地理符号,更像一块心头的陈年老棉被,只是被人扔进了洗衣机,套上了花花绿绿的新布。

咱们先唠唠河南有座叫淇县的小地儿。淇县俩字儿,路过高铁站可能眨眼一瞥就忘了,什么淇,什么县,没个响声儿。但真要往回翻历史账本,这地方最牛掰的名字叫“朝歌”。是的,就是妲己和商纣王折腾出一地鸡毛的那个朝歌。你要是站在老淇河边,风一吹,别说,真能想象当年城池边上甲士林立,宗庙中钟鼓齐鸣。不夸张讲,这地方四百年前还贵得很,风头一度盖过京都。
不过名字这事啊,帝王喜欢改,哪管你百姓愁不愁。明太祖朱元璋给一拍脑袋,把朝歌改成了淇县。朝歌,听起来多仙气,诗一样的地名,谁见谁心动。改成“淇县”,就像做了个冷门的地理选择题。朱元璋改得果断,却也不知道,他那一道圣旨,切断了多少诗意。

要说山多水长的内蒙古,草原上一座老城,包头——这名字初听有点怪味儿。小时候第一次听,就琢磨着这地儿是不是“包着个头”的意思,还是出产包子?后来才知道,包头,蒙古语里就是“有鹿的地方”。可汉语一音译,鹿没了,草原广阔的那点大气也薄了,只剩下个短促的“包头”,不好听也不难听,就是没了辽阔。
可谁还能想象,这座今天近三百万人的工业城,过去其实叫“九原”——多磅礴的名字。九原,聪明点的三国迷马上能联想到吕布,古人的命名果然讲究气势。现在的包头,无论如何跟九原比都差点意思,硬是从豪迈变成了亲民。

历史走着走着,总被皇帝们的避讳搅和——谁的名字不能碰,点谁谁就得让路。石家庄就是这受害者之一。原先那地方叫“恒山”,五岳之一的恒山,气势凌云。结果,汉文帝姓刘名恒,御笔一挥,“恒”字圣洁不容侵犯,于是改叫“真定”。这事说大不大,说小却让一座山从此失去了它的传说。后来为了各种理由又变来变去,最后成了石家庄。你说这名子,实在“庄之有石”,踏实归踏实,却没半点江湖气。
再说说长安,也就是今儿的西安。长安,多牛气的名儿啊,就像中原心脏里跳动的一颗古老的脉搏。多少王朝在这建都安家,多少英雄在这嬉笑怒骂,长安知不知道自己换名是个悲剧?西安二字,坐标倒是明了,可长安里头那个“安”,那份“长久”,又有谁能复制?只怕那景致、那气象、那千年诗意,只能留在历史长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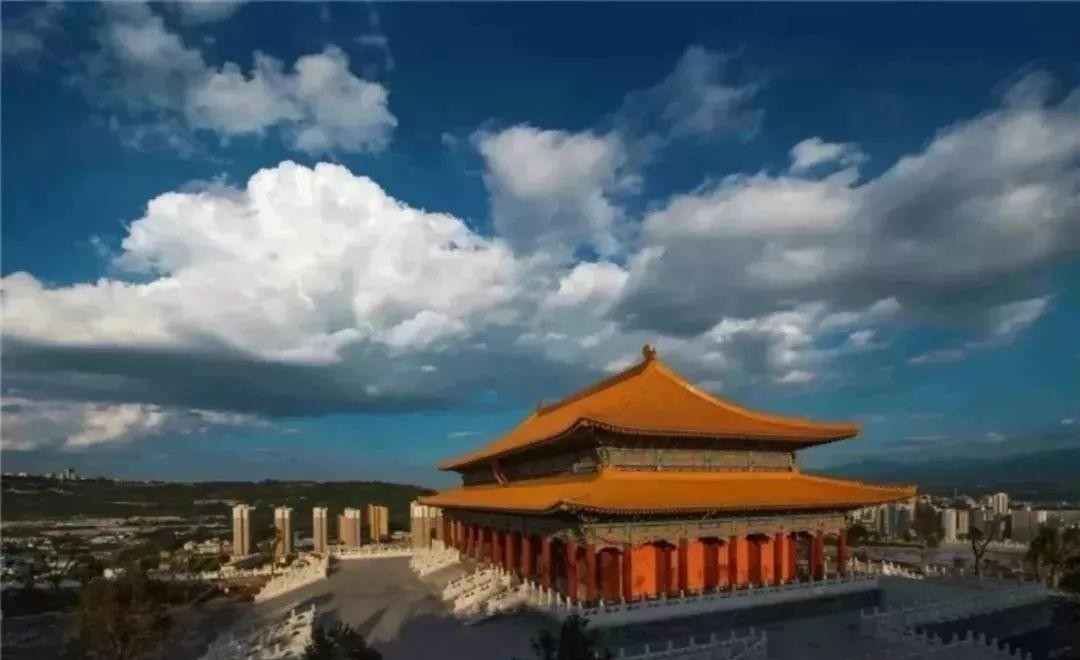
安徽的合肥,也是改名界的“一把好手”。合肥以前叫“庐州”,诗意盎然,庐州月下的小桥流水和许嵩一首《庐州月》都是免费的想象力加成。可偏偏后来改成了合肥。唉,这名字吧,“合着肥”,南方人可能觉得有几分调笑,北方人也觉得有点拗口。你想想,过去庐州提灯夜行,温婉柔美。现在合肥,“两个胖胖欢迎你”,听得都乐了。
走到陕西,宝鸡也是有故事的。现在“宝鸡”二字,老百姓听着亲切,毕竟还有个“鸡”,有食欲。可人家古名叫“陈仓”,光听就气韵绵长,和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一脉相承。可惜明修暗度的传奇只留在脑海,说到宝鸡,谁还记得那一夜风雪、烽火几十里的战事变幻?历史不动声色地把传奇关进了课堂,留下一块接地气的招牌。

再往山东老家走,枣庄。要说枣庄,名字真的像个大号村口。可是这里却怀着一个旖旎的秘密——“兰陵”。这名字气质不输古时美人,兰陵美酒郁金香,文人才子谁不动心?可传到现在,成了“枣庄”,全国网友都说它“土到掉渣”。你想个画面,兰陵王披甲杀敌威风八面,那叫一个潇洒。结果换成“枣庄王”,是不是瞬间变得有点接地气过了头?
其实,这背后的故事多了去了。帝王说要避讳,不许和啥姓啥名重了,你就得改。朝代换了,地盘分了重新命名,不同派头的新主子要立威,想法千奇百怪。有的名字一朝改成庐州、朝歌、九原,你说这四个字就能生出无数诗意;有的却一夜之间掉进了土味里,怎么也找不回来当年那份意蕴。或许,他们都没料到,老百姓记忆里的城市,其实是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温度,是夜里最难舍的炊烟。

你说这些城市的命运被谁安排?就像我们小时候被父母起个小名、被学校老师叫上大名,长大后换了身份证号码,嗯,是不是有点熟悉?挺舍不得的,但也不由分说。那些流传千年、滋养三代的好名字,也许只能在老坟场的草木间,在当地人的心尖上保留下去。走到今天,谁记得“朝歌”不是“淇县”?谁又在意“兰陵”与“枣庄”有什么渊源?还是那句话,名字,总归只是个开始,真正的气韵与故事——都藏在人心里。
你心里最舍不得丢掉的,是哪座城的老名字?还是,最终我们都得学会接受,时光卷走的那些旧称呼,渐渐地也就只剩我们自己还惦记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