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理想,疯癫和没说完的念头

人嘛,谁没做过两个相反的梦:一个是夜里饿得迷迷糊糊,巴不得天裂口缝里落点馒头下来;另一个是白天发呆,想着要是能号令天下该多得意。可真有人把这两个梦合到一起,搅成了一场翻天地覆的大事,打得清朝喘不过气,满世界都跟着揪心。洪秀全就这么横空出世,搅了一锅谁都没见过的热闹汤。
谁能想到,中国几千年老黄历翻来翻去,到了十九世纪,竟也能被一个“穷秀才”弄出花来?说旧社会,旧得牙缝里全是油腻,官老爷光想着刮地皮,百姓穷得叮当响。大伙活着,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掐着嗓子,每天眼睁睁看着希望一丝丝溜走。那会儿要出来个话多的人,说自己梦见了“天父”,说能带大伙分家产、过上好日子,谁还跟你讲什么八股文。

你看,大家伙憋得久了,渴着呢。洪秀全那点说法,乍一听荒唐,细想想又愿意信。啥“拜上帝教”,啥“天兄天父”,弄得挺玄乎,老百姓却觉得,这回可算有人敢把实话明明白白说出来了。这一信,就是一群人。小村子的风刮进了省城,省城的火苗烧到了南京,清朝官府才回过神,发现这不是闹着玩的。
其实吧,太平军这帮人,一开始还真有点铁军的意思。不信你去问问当时的清兵,别管你有大炮还是鸟枪,真打到了一块儿,太平军那劲头像疯了一样,根本不带怂的。有人说太平军能撑这么久,是因为洪秀全手腕子硬。可隔着百年往回瞧,真让太平天国多撑了十年八年,靠的还是他们那一股“抱成团”的劲儿——说句抬杠的话,不就是一群人愿意为一个共同的念头死磕到底。

可这“团结”,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洪秀全这位“天王”,玩的那一套,比乡下传教的还会忽悠,打着宗教名头、讲“天条”、发报恩符,不服也得服。日常管事——连怎么睡觉都要盯着,夫妻不能同房,连夜里打呼噜都得有人查岗。你说是怪也好,滑稽也罢,这就是规矩。有个英国传教士来天京,见了东王杨秀清,还纳闷你们不许男女同宿,难不成都得守活寡?杨秀清倒很得意,说生孩子这事上帝自有安排。要我说,这话在自己家炒菜倒还成,真拿来管万把人,变味了。
有人见过天京的“总圣库”吗?那是太平天国的粮仓,也是他们的心脏。打仗抢来的、吓唬来的、逼捐来的,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扔进去,老百姓吃穿喝都得指望它。这点其实也有两面:一头是“大家有饭就一起吃”,一头却是“有人吃得肚歪,有人光饿得掉牙”。上面说分田分地,下面的官又拦腰截留。一双筷子下去,谁先夹头块肉还得看脸色。

也有种说法,说太平天国这回农民起义能闹成气候,就是比前面几拨人强。秦末的,魏末的,咱们课本从来不陌生。可瞧过去,哪个不是一头热地打进皇宫,转回身就遭自家兄弟暗算,要么断了粮草,兵变四起。可洪秀全这点,倒像个市井里会盘算盘的掌柜,分家产、建制度,动不动就发号施令,还真让他撑过了头几波剿灭。
然而,说到头,纸包不住火,上层过得是灯红酒绿,底层却已经没几个好日子。天王洪秀全称帝了,传说光老婆就有八十来个。住的地方富丽堂皇,名义上讲禁欲,实际上阳台后面藏着三宫六院。要说姐妹们,见了这阵势,谁敢跟他讲理?连传教士都觉得怪得出奇,回到英国后埋头写信,分析来分析去,说这个“新朝代”,其实是“老瓶子装新酒”,迟早还是要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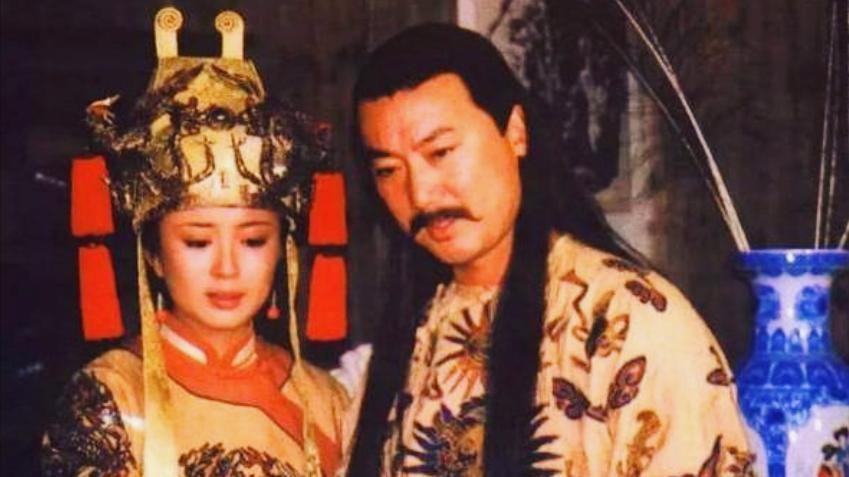
天国标志性的《天朝田亩制度》,光听名字就像是给老百姓的定心丸。书里写的,什么田归天下人、大家一起种、丰收了先自家吃饱、剩下的归公库,其实思路很干净。甚至还提出废彩礼、结婚不论财,细想想,这不就是多数农家打小的心愿吗?但书归书,现实归现实。上层本就自己过着“圣库专享”,底下还敢指望啥?地是分了,可总有人能分三倍,账面是公平,屋里谁都明白。
讲到这,难免让人心里泛点虚火。你说,如若太平天国真能像吹鼓一样,将制度吹圆了,底层百姓吃饱穿暖,哪怕苦点累点,也不会沦落到后来的那种四分五裂。可各路将领光想着自家小金库,谁还真心护那张“理想的皮”?慢慢地,信仰成了笑话,规矩变了笑柄。这场理想和残酷的拉扯,谁又说得清呢?

常常回头想,那些跟着洪秀全起事的人,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是实心眼的信仰,还是一线投机的侥幸?百姓在泥水里苦熬,听天由命。城墙里面,早有人杯盏交错、夜深灯明。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终究泡进了人性的杂质。
太平天国最后没能赢下结局,但它折射过来的火光,却一直不肯散。历史上,我们常说一句话:旧瓶新酒未必新,老梦难圆也难睡。天还黑着,谁也不知下一场光亮,会不会又从何处照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