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多人总觉普通,其实背后故事挺复杂!夏商周那会儿,占据中原的那些人,本质上已经和后来的汉族血脉相连,可偏偏那时候没人说自己是“汉人”,也没人管这片土地叫“汉地”。那时的自称,带着一种自信,甚至有点狂——“华夏”。你说是不是比“汉族”听起来更有冲击力?古人往往就是这样,给自己的名字里加入点理想。

“汉”这个字,起源甚至比我们想得还早。西周晚期青铜鼎罐的铭文里,已经出现了这个字。只是最早“漢”可不是前呼后拥的国族概念,更多是关于河流。甲骨文、金文里左边是三条水纹,右边那一部分复杂,有说是“火”,有说象征别的意思。反正水火交融,流变不息。后来小篆时代变化不大,到汉字简化,右半边变成了“又”,仿佛跟命运有关。这种字的变化,似乎也预示着民族身份的流变,你说巧不巧?“漢”还指银河,夜空中最亮眼的那抹,是不是有点眼高于顶的意味?
有趣的是,刘邦之前,满世界都是“秦人”“楚人”“赵人”,谁要说自己是“汉人”,大约会被笑话。能不能说,正因为后来有了刘邦,才有了“汉族”这个词?《史记》不就写着,项羽做“西楚霸王”,刘邦当“汉王”,住在南郑,管着汉中巴蜀一大块。最终刘邦打败项羽,当上皇帝,直接把国号叫“汉”,顺理成章,“汉人”就有了根。你说给人命名容易,可能持续两千年的人名、族名,是不是只有国家才能做得到?

到了汉朝后,周边国家,包括游牧民族,干脆一律叫中原人为“汉人”。匈奴、鲜卑,好像懒得分谁是关中谁是河东,统统一律称“汉”。唐以后,“唐人”成为南方海外商舶的新名片,不过主流里的“汉”却始终扎根。民间老百姓、朝廷使者,还是喜欢说自己是“汉使”,不分男女老少。这种称呼改变,是不是也和“文化认同”慢慢超过“血统一体”有关?但细想其实有点矛盾,“汉”虽然表面讲文化,骨子里多少还是在和“夷狄”作区分。
秦末混战的时候,谁也没空想这些称谓。项羽尊称自己“西楚霸王”,不叫“楚王”,刘邦那边嗓门也不小。“汉地”只是所有割据势力中一个名字而已。秦始皇更有趣,他创造“秦人”这一概念,三秦大地自有一番气派。可惜他忙着焚书坑儒,没能让“秦人”成为一统江山的永世自称。如今陕西那边,偶尔还有人自称“三秦儿女”,那是怀旧多一点,现实少一点。

要说“华夏”,那更有讲头。西周的贵族,对自己与周边族群的界定,带点小傲慢。在他们心里,“华”意指中原美好之地,“夷”就是落后未开化。这种自我标榜,多少有点自恋,实在也怪不了他们——掌握话语权嘛!华夏,最早根本不是血缘标准,而是文明圈的自我认同。夏商周交替,血统本来就乱作一团,谁能保证周人、商人、夏人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周天子的分封制、宗法制,把王室和诸侯绑得死死的。农奴、奴隶最底层,至于周边“蛮夷”,基本是随缘纳税,归不归心,得靠邻近的诸侯压着。不管怎么说,“华夏”牛气哄哄地代表着中原正统,这种傲慢,后世经常被人诟病,可实际上就是现实的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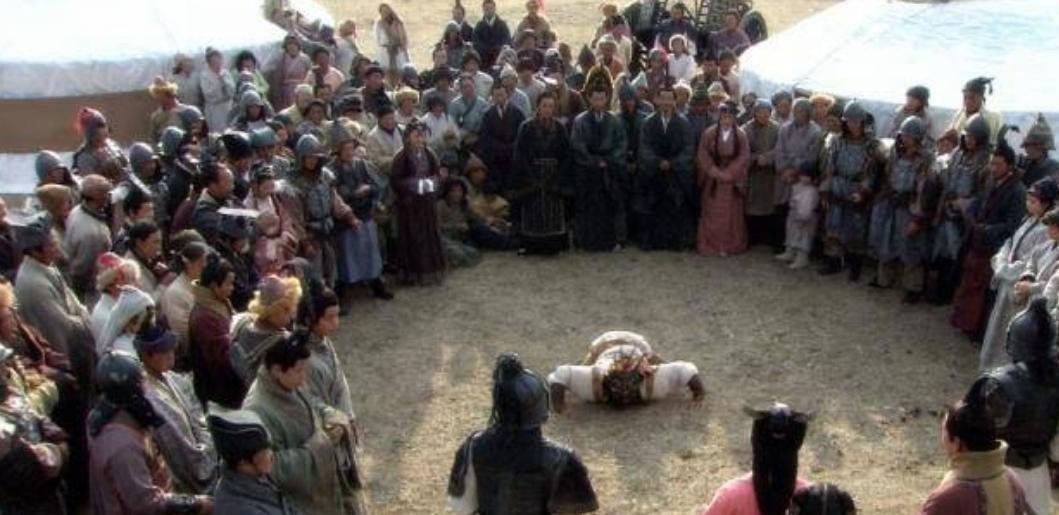
春秋战国时候,各国你杀我争,不但驱逐了王权,还改写了族群的故事。齐桓晋文争霸,赵武灵王却一反常态,公然学习胡人,胡服骑射,直接在服饰、战技上和昔日的仇敌看齐。那会儿很多人说他疯了吧?但效果摆在那,赵国军力飙升,其他几个国家急得直跺脚。赵王模仿“夷狄”特点,把敌人优势吞下变成自己资源,这和后来汉族兼容并包的气质,也算脉络相通。
“华夏”成了对外的联合标签,各国干脆,把周边蛮夷甚至吸纳进自己封国。有的“蛮夷”首领家族,本来就和中原王爷有姻亲。外面喊你“蛮”,家门口喊“兄弟”。说起民族概念,有时只不过是随手一笔,刚说罢自家就是“正统”,转头说别人也没错。矛盾吗?一点都不。事实就这么乱。

汉武帝时,汉朝才算真正一统,经济、政权、文化彻底合一。“郡国并行”变察举制,拔高人才流动。下层起家的天子,喜欢从各地举荐能人。科举的雏形,实际上从汉武帝那一脚踢开大门。之前的贵族“封闭”,后来全挤进来,天下皆有机会。这要说完全打破门阀壁垒,可能言过其实,但一点点松动,各类身份混融,也是事实。
经济上一刀切,货币统一,五铢钱印遍全国。原本各地“土货自己卖”,彼此买卖交流少。到了汉武帝,市场连通,商队往来,钱币价值统合。财政收入增加不止一点半点。你说这钱到底是买卖带来的,还是政策推动,或许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没人会否认,国家大一统时钱才好用。

文化整合也同步进行。汉武帝招贤纳士,儒家学说进官方大堂。百科人才从各地来,学成后各自返乡,做地方教师,文化一脉相承。大家都讲汉语、写汉字,以“汉文化”为荣。底层劳动者未必懂这些,但基层治理靠这个体系运转,久而久之,谁还问出生地是哪省哪州?“汉人”自信是慢慢长成的。
但你要说“汉族”绝对没有血统因素,还是说不过去。有时候讲“汉族”是文化、是认同,但千百年来族群融合几乎永不停歇,蒙古、鲜卑、契丹,后来都逐步融入汉族。你说汉族没有固定的血缘,事实摆在那儿。可是“汉族”真能纯粹靠文化维系?有人说能,有人说不能。到底哪个是真话?

在民族认同和实际血缘之间摇摆,其实也反映出另一种灵活。不像犹太人、日耳曼这种讲究族谱,汉族成分变变又算什么?大一统国家里,“汉族”变成口号,不分先来后到,归根到底叫“天下一家”。不过每逢军阀混战,地方又重新分省分族。统一与割裂,往复轮回。哪个才是自然的状态?
很有意思,真正消除汉夷对立,始终做不到。每次融合都是利益驱动,王朝更替或者疆土拓展,才有强力机制促进通婚、通商、通学。老百姓骨子里对“夷狄”还是有三分戒备,官员嘴上说尊重平等,背地里轮不到他管。

其实汉族的身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外来民族进入之后,官方常以“编户齐民”方式对待。你分得清谁是哪朝遗民、哪个名门后裔?或许只有家谱认得。百姓根本不会去考究,“大汉王朝”成为默认身份,只要听得懂官话、穿得上棉衣,人人可做汉家人。这种融洽未必牢靠,却有顽强韧性。
说到“华夏”,那个时代的中原人未必会认同今日的“汉族”,但骨子里有同样的血气:自信、张扬、认祖。无论如何划分族群、转变称号,身份本质常常依随权力流转,体系更迭。有人觉得“汉族”这个名字有些淡了,“华夏”更提气;有人反而珍惜“汉族”长久不易,图安生图团圆。哪种对哪种不对?反正人心就是如此善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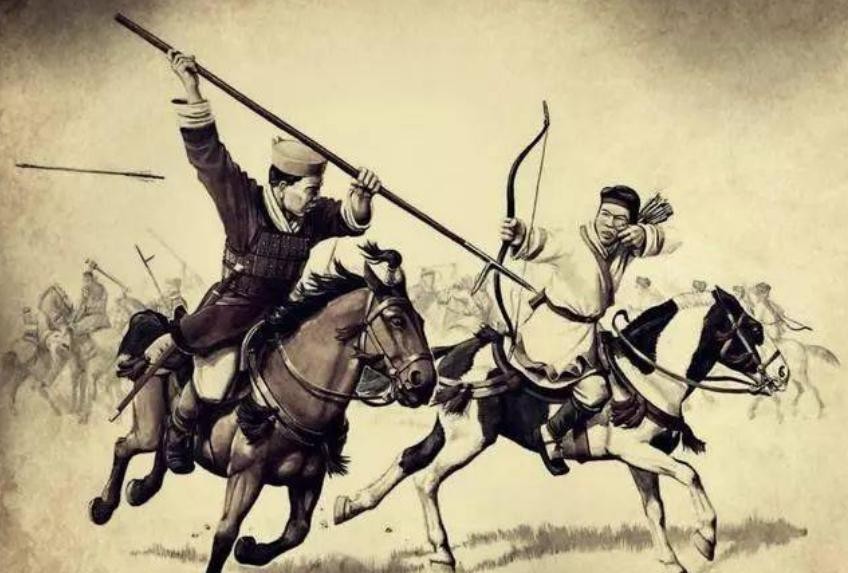
**总归一句,从起初的“华夏”,到后来的“汉族”,名字里折射的不止是地理和亲缘,更是一种对故土、对文明的连续守望。赞也罢,弃也罢,每一代都在留与变之间寻找新的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