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 作者 方志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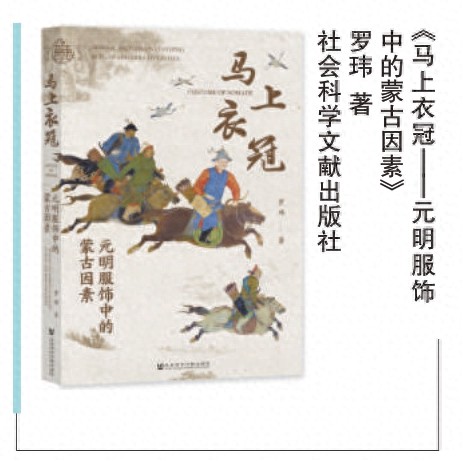
“民以食为天。”但是,在“衣食住行”人类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中,为何排在首位的不是“食”而是“衣”?
因为“衣”是“文明”的人类与“野蛮”的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食”代表的是生存,所有的动物乃至生物都需要;“衣”代表的是文明,甚至可以说代表着文明的程度,只有人类才具有。只是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对“食”即生存的关注更多,对“衣”即文明的关注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或多或少有“观念”的问题,即认为“食”是不能少的,“衣”固然也不能少,但“服”上加个“饰”,就有些“奢侈”了,而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勤劳朴素的,是不能追求奢华的。虽然追求奢华不一定好,追求“美”却是人类乃至生物的共性。所以,人类的服饰既体现了文明程度,还表现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一种文化的表现,用时髦一些的表述,是“物质文化”“物质文明”的体现。
罗玮和他的《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一,以往关于古代服饰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采用“历代服饰史”即“贯通”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是限于某个具体朝代即“断代”的服饰形制研究。这两种服饰研究模式皆有其合理性,而且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问题也是明显的。“贯通”式研究容易止于表层,往往只是在进行服饰形制等物质研究之后便浅尝辄止,并不涉及服饰背后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断代”式研究的视野专注,却容易忽视服饰本身所具备的长时段、跨朝代继承和延续的历史属性。本书在前两种服饰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既不谋求“贯通”于中国历代,也不局限在某个“断代”,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角度,关注蒙古服饰对中国服饰本身和文化内核的影响。
其二,本书选取元、明两代作为服饰问题研究的基本时段,对蒙古服饰传统在元、明两代数百年长时段的影响和流播遗存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一章“马上衣冠: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探讨了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分别对钹笠帽、后檐帽、辫线袄、答忽与半臂、质孙、兀剌靴、云肩等十三类元代影响较大的蒙古服饰进行了研究。第二章“汉世胡风:明代服饰中的蒙古遗存”探讨了以上诸种蒙古服饰因素在明代社会中的存在、传播和流变状况,并尝试对其行用阶层人群、行用原因、社会心理以及所反映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进行初步探讨。第三章“遗俗流变:蒙古服饰的深层影响”初步探讨了明代士大夫对蒙元服饰遗存的认知,揭示了所谓清代满洲服饰,其实很多是蒙古服饰在元明两代流变的结果。
其三,本书广泛收集和研究大量实物、图像和文献史料,在一百五十多幅各类图像中,许多为第一次在服饰研究著作中展示。这些实物、图像、文字材料证明,元朝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相反,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清代。
其四,在古代服饰研究史上,本书首次将元、明两代的服饰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系统探索其中的蒙古影响因子,充分体现跨朝代、长时段的研究突破。本书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强调多种史料互证,文字与图像并重。本书较之于传统工艺美术模式的古代服饰史研究,更加突出了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本书附录部分专门精选出有关的史料,这是以往服饰史著作所不具备的。
本书的现实意义也是非常突出的。近年来古代服饰研究不断深入和得到热捧,与年轻一代中“汉服文化复兴”的社会现象有密切关联。因此本书的写作缘起,除了根植于学术思考,同时也含有现实关怀。那就是让本书的研究成果惠及当今“汉服热”风潮下的广大青年人,引导他们的思想,纠正他们的偏颇,实现学术与社会的良好互动。
和一般的著作不同,本书并没有把“绪论”而是将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记载置于卷首,可以立即引发读者的关注,可谓别出心裁。略举两例:
况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明武宗实录》)
正德皇帝朱厚照之所以得到“武宗”的庙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尚武”。他在宫中喜欢和宦官、勇士中的高手过招,在边境喜欢找蒙古人切磋,所以多次率领京军、边军与蒙古鞑靼人角逐,并自称亲手格杀了一个蒙古骑士;听说江西宁王谋反,他立即率领大军南下,要与宁王在鄱阳湖决战。所以,尽管文官们说“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但武宗却认为,只有以这样的服饰迎接,才能显示出自己“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身份。
今通用者又有陈子衣、阳明巾,此固名儒法服无论矣,若细缝裤褶,自是虏人上马之衣,何故士绅用之以为庄服也?(《万历野获编》)
这里所谓的“陈子衣”,当是名儒陈继儒的服饰。而所谓的“阳明巾”,则是传说中王阳明所戴的头巾样式。可见明代服饰的多元化,既有名儒之服饰,又有“虏人”之戎装,各取所需。民族的交融,从来不是所谓“落后”用武力征服“先进”、“先进”用文化改造“落后”那样绝对化,民族的交融、文化的融合是双向乃至多向的。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开始习惯定居与农业,习惯读书与科举,汉人同样崇拜蒙古人的尚武乃至斗狠,而蒙古“马上”服饰,正是尚武的标志。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