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八的永州汽车站,五个打工者中就有三个攥着去广东的票。
湖南14个市州去年常住人口数据刚出炉,除了省会长沙,其余都在失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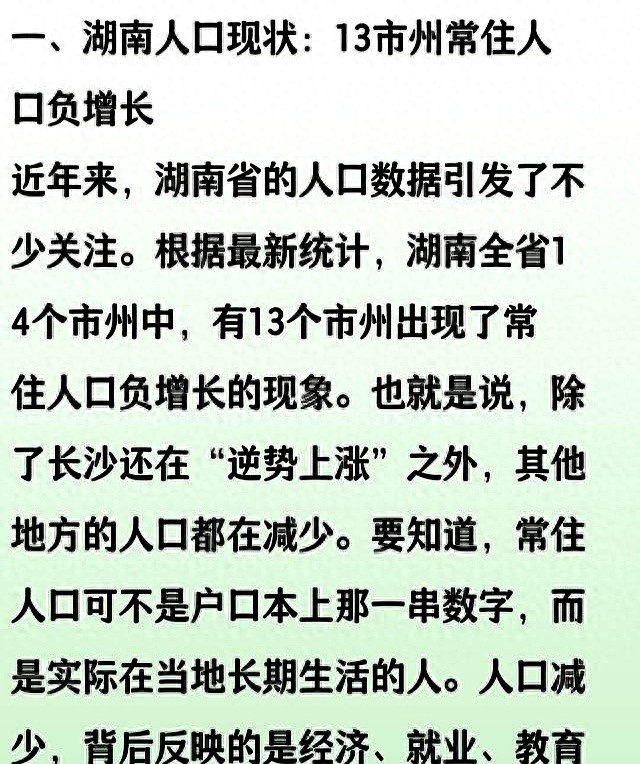
永州十年跑了五十万人,邵阳的小镇青年甚至发明了“春节迁徙症”这个词——指每年过完元宵就得治的离乡病。
当高铁把省会到地级市的通勤时间压缩到两小时,虹吸效应正在重塑八百里洞庭的城乡图景。

奶茶店招聘启事在县城挂了三个月无人问津,教培机构撤走后空置的商铺成了麻将馆。
那些在深圳富士康拧螺丝的年轻人,周末能去看周杰伦演唱会,回老家反倒要面对亲戚们“读了大学怎么还回来”的灵魂拷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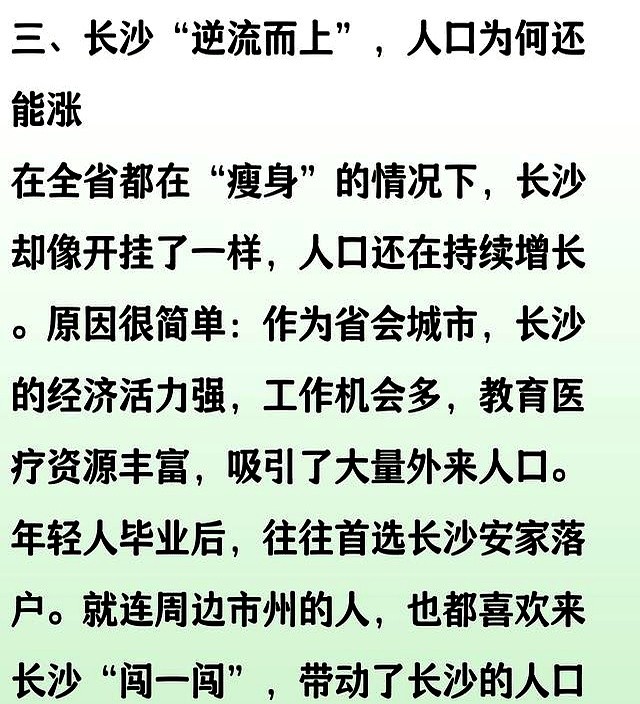
长沙五一广场凌晨两点的霓虹灯,照见的不仅是网红城市的繁荣,更像一盏吸顶灯抽走了周边城市的活力。
当三甲医院和重点中学都集中在省会,地级市的家长们不得不用学区房首付换张进城高铁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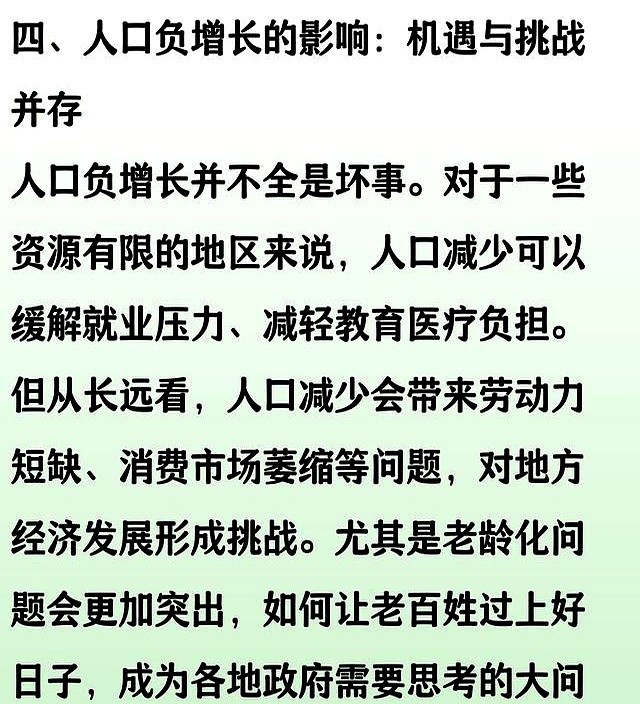
高铁线越密,小城心跳越弱。
去年邵阳某镇小学六个年级凑不齐一个班,校门口的油菜花田倒是被开发商圈成了“省城教育大盘”广告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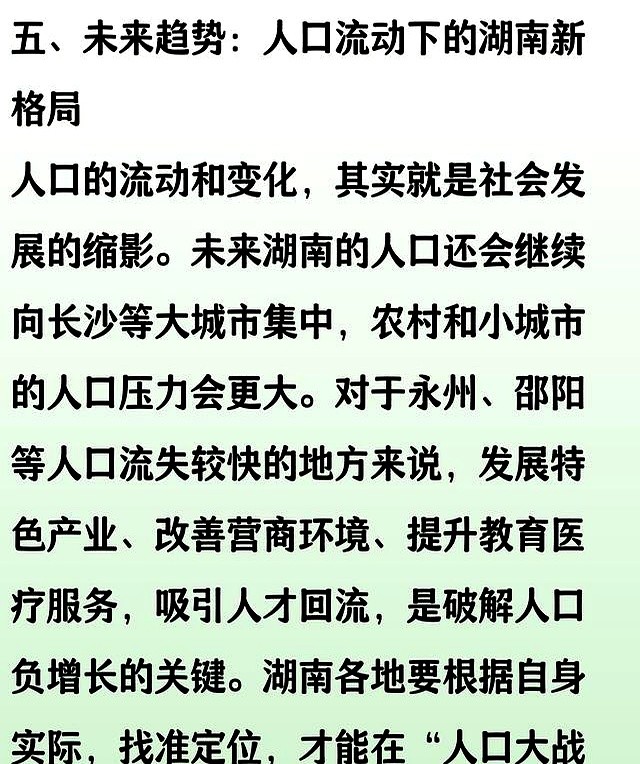
那些留守老人手机里的家庭群,置顶的都是孩子从东莞、长沙发来的都市夜景。
当乡村振兴遇上地铁通勤圈,县城正在变成省会的生活阳台——春节晒腊肉,平时晾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