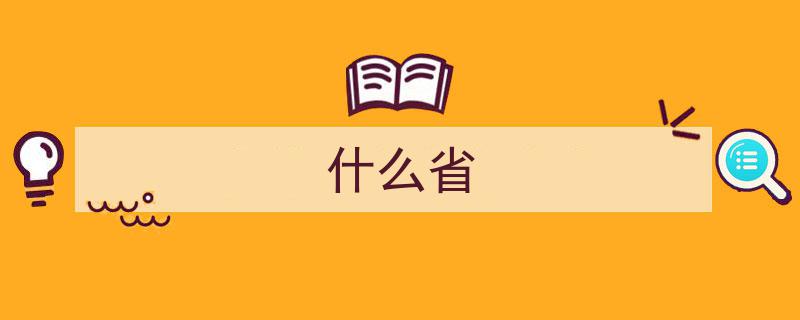你可能听说过河南的范县,也可能没听说过。但是你一定不知道,这个县城居然在山东境内,完全被山东包围,跟河南没有任何交界。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县城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被称为“全国一大怪”的县城的故事吧。

要是没去过,你很难想象那种“站在山东地里,办着河南事儿”的错位感。我第一次拐过去,是被导航带的路,车刚要进城,前面就是山东那边的卡口,后备箱打开,警察客客气气,但你心里总觉得,这是出省了吗还是没出省?一抬头,路牌写着“范县”,心里又咯噔一下:原来真有这样的地方。
咱们把时间往前拨。范县的年头长得很,名头也老,名字跟南边那条范水有关。它像个在边界线上来回挪椅子的孩子,先跟着河北走过一段,后来拐到山东那边,再到更早更早的时候,被称作濮州、东平路之类的管辖,说白了,谁家袖子长、手伸得过来,它就搭谁家的肩。明清、民国那会儿,基本算山东的地盘。

说到名人,范县也不是默默无闻。郑板桥那会儿来这儿当过几年父母官。你想象他从扬州那边带着“怪”味儿的笔墨来到这个难处小县,修堤、劝农、开仓施粥,民谣里都还留着他“难得糊涂”的影子。县衙的砖墙被风吹得发白,正厅上头挂过他的匾,这些旧事如今都成了游人喜欢讲的小段子。
真正让范县“变戏法”的,是1964年。那一年,黄河脾气大,河南、山东两边为水闸怎么开、堤坝谁修差点儿把嗓子喊哑了。上面一拍板:这边那边互相“换块地”,东明那边划给山东,寿张划到河南,同时把金堤以南几个区划进范县,留作将来泄洪用。棋盘子一挪,格局就变了——范县在行政上摇身一变成了河南的孩子,可它的老县城没动窝,还待在山东的怀里。

于是出现了全国少见的一幕:河南的县城,四面八方都是山东地,像被人用圆规圈住了一样。外面是莘县樱桃园镇,里面是范县县治,隔了一圈地界,彼此看得见。当地人自嘲:“咱这县城,是安在省门外的。”更俏皮的说法是:“鲁地揣着个豫县,豫地又兜着个鲁乡,乡里还套了个豫村,村里住着鲁人。”听着像绕口令,但你要真住在那儿,它不是笑话,是日常。
日常是什么?比如出趟城门,你就等于过了一回省界。以前最麻烦的时候,拉着菜去隔壁乡镇卖,来回都要跟两个地方的执勤打招呼。孩子上学报名,老师填籍贯,班里的人乐呵半天:你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家里座机有意思,拨山东号能响,拨河南那边也能通,两个区号在一个客厅里打架。邮递员老王有次玩笑说:“给范县投件,最怕写得太细——越细越绕。”

为这份“绕”,范县后来做了一个痛快的决定:另起炉灶。1995年,县里定下一个新城区的计划,把政府机关、学校、医院这些“筋骨”慢慢搬过去,带动居民往新地方落脚。新旧之间,就用一个名字简单划开——十字坡。坡以南十来里,是新城;坡以北十来里,是老城。老城收住一口气,新城开窗换风。
几年几年地盖楼、铺路、栽树,新区像是从地图上“长”出来的。到了晚饭点,文体馆旁的广场上,扇子舞一排、拉丁操一排,小商贩吆喝,孩子们追着泡泡跑,一圈一圈的,像新生活的涟漪往外铺。你要是清早过来,街角那家胡辣汤热气腾腾,白瓷碗里满是椒香;蒸笼一揭,包子皮薄肉实,蘸一口蒜泥,整个人都醒了;再来块牛肉盒子,出门的时候袖子上全是芝麻香。周六清晨,从郑州上高速,两小时多点儿就能摸到这个新城的边儿,跟着导航慢慢往里挪,城的骨架已然有模有样。

你说这地方发展靠什么?靠的还是那条河给的土与势。黄河边上的地,种小麦、花生、玉米,风一年比一年稳,粮仓不缺饭。后来工业园区也扯起了帆,先是食品加工,再到装备制造,慢慢叠起来一张“饭碗网”。新城区一条主街,商场亮得扎眼,夜里还有露天电影,来逛的人多了,烟火气就起来了。
别看地理位置别扭,文化这根筋一刻没断。板桥的故事,是范县人最愿意讲的“家底”。老街头有人拿竹简形状的小印章给你摁字,一边摁一边说,板桥当官不苟且,写字带风骨。另一端,是冀鲁豫边区的那些印记,旧址、纪念馆、红色小路,清明和暑假,领着孩子来的人不少,讲讲曾经的日子,讲讲这块地怎么挨过苦、熬过荒。外面的人来,吃口胡辣汤,听两段乡音,往往就开始明白:这个“飞”在外头的县城,心口上的脉搏是一点不乱的。

当然,有些坎也不容易跨。你要问老城里的人还搬不搬?有人说舍不得,祖坟在那边,槐树也在那边,夏天风一过,花絮像雪一样;也有人说该走,孩子要上更好的学校,医院在新区,路也宽。一个县城,摆在两个选择的秤盘上,谁都不肯真说死。其实,这就是人生:你在原地扎根,也在远处望着灯。
那年我绕回老城,樱桃园镇那头太阳落下去,墙上的影子把电线杆拉得很长。有个老人坐在门槛,手里攥着一团手绢,跟我说:“我们小时候常背的一句话,现在还管用——不管写哪个省,到了饭点儿,锅里得有气。”他笑,说锅里有气就是有烟火、有希望。这个“气”,在范县的老城新城之间,传得挺稳。

有人问,范县的“怪”,到底怪在哪?在地图上看,是怪;在人心里看,是活法。它被地理放在一个不太舒服的位置上,却又拿出办法,搭了一个能住人的家当——修路、迁治、拉产业、讲故事。年复一年,县城像个被风吹打过的汉子,牙咬得紧,脚步不乱。
如果你只想找一个结论,那可能会失望。范县要不要把县城彻底“转回”河南?莘县那边又该怎么配合?这些问题留在现实里继续发酵,像一锅小火慢炖的汤。我们能做的,是在地图上别急着下判断,走到地上去看看:路边摊上热气正冒,广场上乐曲正响,孩子们追着泡泡跑。人在哪儿,城就在哪儿。至于省界那道线,有时候,它只是一条需要耐心对话的褶儿。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