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期,数十万建设者涌动井陉大地,谱写建设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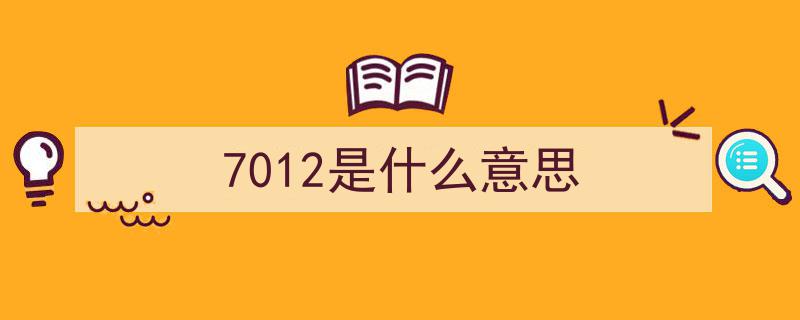
您描述的这段历史,指的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修建"井陉煤矿"(特别是其核心部分"井陉矿务局")而涌向井陉大地的数十万建设者。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奉献的时代缩影:
1. "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发展煤炭工业以支持工业化建设。井陉煤炭资源丰富,是国家重点开发的矿区之一。
2. "建设高潮:" 1953年,井陉矿务局开始大规模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技术人员、工人、复员军人等数十万人响应国家号召,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来到了这片相对贫瘠但资源丰富的土地。
3. "艰苦创业:" 这些建设者们克服了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在荒山野岭上开天辟地,修建矿井、厂房、铁路、公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他们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新的生活。
4. "精神象征:" 他们的奋斗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是“井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见证。
可以说,井陉大地见证了新中国早期工业建设的光辉历史,这些数以万计的建设者为井陉的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
相关内容:
千年古县井陉,听起来像传说里的名字,是2005年国家点名的千年古县——人家不是自封的,是正儿八经认定的。从地图上看,它就像一口井,被太行山的胳膊圈起来,西边和山西打个照面,东边倚着华北平原,娘子关一伸胳膊也能摸到。这地方光听名字就有点意思,别急,后头还有更多故事。
小时候我常听老人说,井陉是个“塞”,分分钟能打仗的地势,传说背水一战就在这,那会儿庄子河畔,兵马嘶鸣,谁还顾得上诗意?但其实,大多数井陉人的日子都是在厂矿里把日子熬出来的——你说这地方,山高水远,怎么就变成了电机轰隆的热闹县城?这事还得从“微水发电厂”聊起。
微水发电厂,若你在七十年代走进井陉,那绝对是最抢眼的位置。工厂门口热乎乎的早点摊、下班后家属区里孩子们的吵闹,还有某个傍晚里,工人们拎着工具箱、衣服上还有油污,迈着瓮声瓮气的步子回家。我那会儿小学同学一半家里都是这电厂的人,一起写作业的时候,屋里总蒙着一层煤味儿。也许你不懂,那时候“厂里的”身份挺体面,但后来一纸政策,有人就此告别井陉,被分流到西柏坡,甚至远走呼伦贝尔。那些人有的是骑着旧自行车走的,有的是抱着小孩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如今电厂楼还在,空空如也,却有几棵老槐树还记得孩子们曾经叠过纸船。
说到工厂,井陉可不止发电一条路。五六十年代,国家的步子走得急,军工厂3502、3514接二连三落地,有的叫402,有的索性叫401,名字那么神秘,连街坊都只能猜,谁在里头干什么。那些从北京、天津来的年轻人,扛着大背包,憋着眼泪上车。有工人在黄土坡上建新楼,也有人在零下十度的冬天盖能挡风的家属区。一个个厂区像星星落在山沟里,刚盖好的教学楼还带着水泥的新味。工人们写家书,一边抱怨这地方连干菜都要抢着买,一边夹杂着难得的骄傲,“我们这厂子,可上了国家计划。”
再来聊聊五四二工程,代号7012。听名字像谍战片,其实也是那段岁月的符号。秀林镇突然热闹起来,穆村、南王庄,都成了穴地里点火做饭的地方。一桩桩老砖厂、一辆辆生产队的破拖拉机,为几座分厂添砖加瓦。五湖四海的人来了,四川的、东北的、广东的,全挤在同一个澡堂里打水。有老人还记得,头一年冬天冷得掉牙,可第二年新工厂开工了,孩子们能穿棉衣,外乡人不再算作“外人”。只是这热闹没过多久,20厂搬到正定,和铁厂合并成了河北铸造公司。然后归于沉寂,厂门紧锁,留下几栋红砖楼随风飘雪。
井陉的厂子,多得数不过来。什么石家庄铝厂、玻璃厂、印染机械厂,一串串编号8130、4511——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厂,曾经让整个山区沸腾。你要是遇到老井陉人,问他们,那哪家厂饭票最好使,哪儿的澡堂最宽敞,他们能聊一天。可惜,好景难长,有的厂早已人去楼空,门牌生锈,窗子上的防盗网里灌进了枯叶,变成了“忘了扒门的过去。”
当然不光是工厂,还有部队。井陉一度是部队和仓库的集散地,编号随处可见,什么5927、811、6605,一听就不是凡人能进的地方,医药储备仓库6771更是高度机密。威州镇的6410工厂现在还坚守在井陉,只是外头的世界已今非昔比,昔日的山沟沟变了样。你要是翻老照片,能看到士兵在库房门口晒太阳,挺着钢笔裤,军帽扣得端正。现在这些库房大多封了门,有的甚至成了无人问津的记忆。
井陉不是一朝一夕就变。你要是站在县城广场望出去,看见高速公路像银带一样穿肠而过,井石快速路一路通到石家庄,汽车吼叫,灯火通明。说以前井陉是穷山沟,那是有点夸张,但真要说“日新月异”,这些年是真的赶得快。那些老厂房,有人改成了咖啡厅,有人挂上了三层玻璃门,楼底下卖羊汤。新楼拔地而起,孩童在广场放风筝,电厂旧址上盖起了小区,仔细看还能见几块写着编号的老水泥块。
至于那些被井陉吸引、或者被政策带来的外地人,他们其实有着最复杂的情感。有人成了地道井陉人,子女扎根于此;也有人搬走了,偶尔会在节日驱车回来,绕着老街走一圈,买个煎饼果子,顺手拍张照片发到旧同事群里。往事如烟,谁又记得当年楼下小卖部的煤球炉子、谁家铁饭盒掉在水沟?
我们常说,历史就是翻篇,但对于井陉这样的小县,历史是像家里老虎皮箱底下藏着的粮票,有点潮湿,有点温热。究竟那些曾在这里打拼的人,他们的心里还留着多少井陉的影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子变了,但井陉人的韧劲和念想,大约不会消失。
我偶尔也想,是谁造就了今天的井陉?是那些舍家别业来开厂的工人?是曾在背水一战的边塞挥刀的士兵?还是无数写着“代号”的仓库、部队?也许他们都没想过会被后人记住,但风吹过太行西麓,电厂的老楼静静等着,有一天,归来的游子会驻足片刻,翻看一眼岁月。
井陉的故事,还有太多没说完的细节。你说,等有空,咱们再聊点别的——比如谁家的老厂长,冬天喜欢在院里晒被子。历史其实,就是一群人在山水之间,熬出了碎金般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