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之行——午餐五重奏,扬州美食之旅的味蕾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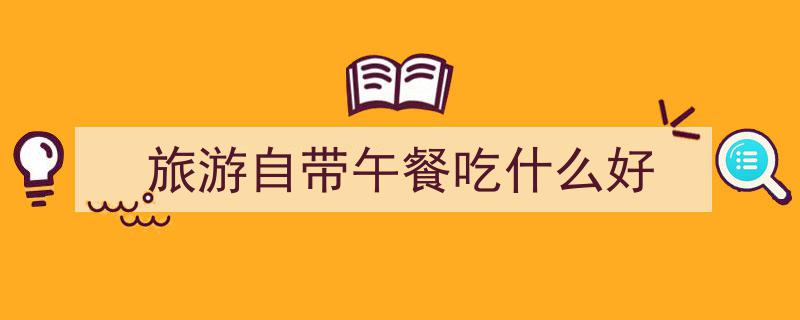
我们来续写“扬州之行——在扬州的午餐(五)”。
---
"扬州之行——在扬州的午餐(五)"
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略显疲惫但依旧兴奋的旅人身上。经过前几日的寻味,我对扬州的美食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愈发期待这最后一顿午餐,希望能有新的惊喜,或是完美地收尾。
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一家在当地颇有口碑的老字号淮扬菜馆。从名字就能听出几分古韵,门面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张扬的精致。门口常常排着队,足见其吸引力。
"【环境氛围】"
一踏入店内,一股混合着饭菜香和淡淡木头的气息扑面而来。不同于前几餐的喧嚣或精致,这里的环境显得更为家常,却又干净利落。原木色的桌椅,墙上挂着几幅扬州风景画,服务员穿着朴素的制服,忙碌而不失礼貌。这种恰到好处的氛围,让人能放下心神,专注于即将到来的味蕾体验。
"【菜品呈现】"
服务员很快上来了菜单,依旧是那熟悉的淮扬风味,我们根据之前的经验和对新品的向往,点了几个招牌菜。
1. "清炖蟹粉狮子头 (Qīng Dùn Xiè Fěn Shī Zi Tóu - Clear Broth Braised Pork Balls with Crab Roe):" 江浙
相关内容: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精准地丈量着我们家微妙的平衡。新闻联播里字正腔圆的播报,盖过了妻子林岚在厨房里洗碗的哗哗水声,也盖过了我心里那一点点正在滋长的烦躁。
我爸顾兆祥雷打不动地坐在沙发正中央,那是他的“龙椅”,身体微微前倾,眯着眼,仿佛要把自己嵌进屏幕里去。他耳朵有点背,35的音量对他来说刚刚好,对我和林岚来说,却是一种绵长而持续的折磨。
我起身想去倒杯水,下意识地绕开了茶几,那里堆着我女儿盼盼的乐高积木。经过书房时,我鬼使神差地拉开了那个许久没动过的抽屉,想找一找旧的充电线。指尖划过一堆杂物,却触到一张硬卡纸的边缘。我抽出来,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上面的父亲比现在年轻太多,穿着板正的中山装,身边站着一个眉眼与他极为相似、却又透着一股桀骜的年轻人。我不认识他。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两个字:建军。
“顾明,你傻站着干嘛呢?赶紧把你爸的降压药拿出来,他今天又不记得吃了。”林岚擦着手从厨房出来,眉头拧成一个结。
我把照片塞回抽屉深处,关上,像藏起一个不属于我的秘密。“哦,来了。”
饭桌上的残羹冷炙还没收拾,我妈正慢吞吞地用抹布擦着桌子,动作迟缓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看到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瞥了一眼客厅里专注看电视的父亲,又把话咽了回去。这种反常的沉默,像一根细小的鱼刺,卡在了我的喉咙里。
“妈,怎么了?”我轻声问。
“没……没什么。”她躲闪着我的目光,“你爸他……他说明天想跟你商量个事。”
第二天是周六,我难得不用上班。早饭时,父亲清了清嗓子,放下了筷子。这个标志性的动作一出现,我就知道,“正事”要来了。
“顾明,”他看着我,眼神异常严肃,“我想回一趟扬州。”
“扬州?”我愣了一下。我们家祖籍扬州,但自从我记事起,就再没回去过。父亲对这个话题向来讳莫如深。
“嗯,”他点点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下周末就去。你跟林岚,还有盼盼,都请好假。”
林岚正在给盼盼夹鸡蛋,闻言手停在半空:“爸,怎么这么突然?扬州那边还有亲戚吗?”
父亲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像六月的天。“叫你去就去,问那么多干嘛?”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我妈赶紧打圆场:“哎呀,你爸就是想家了,老了嘛,都这样。回去看看也好,就当带盼盼旅游了。”她转向我,带着一丝恳求,“顾明,你爸他……其实早就想回去了,就是……”
她的话又说了一半,父亲一声用力的咳嗽,让她把后半句硬生生吞了回去。那句未完的话,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餐厅闷热的空气里。
我看着父亲倔强的侧脸,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有些刺眼。他为什么要去扬州?那个叫“建军”的年轻人又是谁?我忽然有种预感,这次扬州之行,不会只是一场简单的故地重游。它像一个被强行按下的开关,即将启动某个尘封已久的家庭机器,而我们每个人,都将被卷入它轰鸣的齿轮之中。
第一章 尘封的信件
周末很快来临。关于去扬州的决定,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们家激起了持续不断的涟漪。林岚嘴上没再反对,但脸上的不情愿几乎可以拧出水来。她私下里跟我抱怨:“你爸也真是的,说风就是雨。公司最近忙得要死,我怎么可能说请假就请假?”
“就当陪陪老人吧,他难得提一次要求。”我只能这样安抚她。其实我自己心里也直打鼓。父亲的反常,母亲的欲言又止,还有那张神秘的照片,都让我感到不安。
我的核心缺陷,就是这种该死的“维持表面和平”的惯性。我害怕冲突,总想把所有矛盾都用“算了算了”、“都不容易”这种话术糊弄过去。可我知道,这种粉饰太平,迟早会迎来更猛烈的爆发。这次扬州之行,就是第一个征兆。
出发前一晚,家里乱成一团。母亲在给父亲收拾行李,一件件旧衣服叠了又拆,拆了又叠,嘴里不停地念叨:“这个薄了,那个颜色不好看,回老家要穿得体面点。”
父亲则坐在他的“龙椅”上,对着35分贝的电视充耳不闻,手里拿着一块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他那副老花镜的镜片。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每当他心烦或者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我粗略算了一下,从决定去扬州到现在,这个动作的频率至少增加了三倍。
“爸,我给你买了部新手机,智能的,下个导航,到了扬州也方便。”我把一个新手机盒子递过去,想缓和一下气氛。
父亲抬起眼皮瞥了一眼,眉头皱得更深了:“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我用我的老年机就挺好,字儿大,声音也大。”
“爸,现在出门都用这个,查地图、买票,方便。来,我教你。”我耐着性子打开手机,点开地图应用。
“你看,点这里,输入你想去的地方……”我把屏幕凑到他眼前。
他一脸抗拒地别过头,嘟囔着:“看不清,太复杂了。”
“不复杂,你学一下就会了。”我放缓了语速,像哄孩子一样,“你看,这个小蓝点就是我们,你想去哪,它就带你去哪。”
他哼了一声,不说话,但眼睛却偷偷往屏幕上瞟。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就是这样,手把手地扶着我的自行车后座,嘴里说着“自己骑,摔不倒”,但手却一直没松开。我的鼻头莫名一串酸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教我走路的人,如今却要我来教他如何跟上这个世界。这或许就是轮回。
“行了行了,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研究。”他挥挥手,重新拿起他的老花镜,用力擦了起来。
我叹了口气,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这时,盼盼跑过来,举着一幅画:“爸爸你看,我画的我们全家去扬州玩!”
画上,太阳笑得很大,我们一家人手牵手,旁边还有瘦西湖和五亭桥。我笑着摸摸她的头:“盼盼画得真好。”
“爸爸,为什么爷爷画得不开心啊?”她指着画上的爷爷,那个小人儿的嘴巴是往下的。
孩子无意识的一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在场所有大人的心脏。我看见母亲的肩膀垮了一下,林岚的脸色也变得复杂。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约2000字处)
我知道,有些家庭的平静,不过是靠着一个孩子的童言无忌来戳破的。林岚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责备,也有无奈。她低声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忍耐的地方。”
深夜,等所有人都睡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进父母的房间,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的东西。父亲的那个老旧的棕色人造革行李箱放在墙角,锁扣已经坏了,用一根布条系着。这是他当年从扬州来我们这个城市时,唯一的家当。
我蹲下身,鬼使神差地解开了布条。箱子里都是母亲叠好的衣物,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和旧时光混合的味道。我伸手进去整理,指尖却触到了箱底一块凸起的硬板。我掀开那层作为底衬的硬纸板,下面竟然还有一个夹层。
夹层里没有钱,也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我打开它,里面是一沓厚厚的信。信封已经泛黄发脆,收信人的地址都是同一个: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xx号,顾建军(收)。
顾建军!又是这个名字!
我抽出其中一封信,展开信纸。父亲那手刚劲有力的字迹,在昏暗的台灯下显得格外沉重。
“建军吾弟:见字如面。离家一别,已是三载。沪上冬寒,然不及我心中之冷。父病重,速归。兄,兆祥。”
落款日期,是三十五年前。
我一封封地看下去,时间从三十五年前一直延续到二十年前。内容从最初的催促、争吵,到后来的解释、恳求,再到最后的独白与思念。每一封信,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砸在我的心上。
原来,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叔叔。原来,父亲那份深藏心底的倔强和沉默,背后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家庭伤口。这些信,全都没有寄出去。它们静静地躺在这个箱子的最底层,像父亲从未说出口的歉意和悔恨。
我忽然明白了,这次扬州之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是简单的叶落归根。这是一趟迟到了三十五年的赎罪之旅。而那个所谓的“午餐”,或许就是父亲为自己准备的,一场不知能否等到客人的审判。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心脏怦怦直跳。这时,走廊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我吓得一激灵,赶紧合上箱子。是母亲,她起夜,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
“怎么还不睡?”她小声问。
“……没什么,看看爸的箱子还能不能用。”我撒了个谎。
她叹了口气,走到我身边,看着那个箱子,眼神悠远。“你爸的脾气……唉。”她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开长途。”
我点点头,看着她蹒跚地走回房间。我知道,她一定也知道这些信的存在。这个家里,似乎只有我、林岚和盼盼,是被蒙在鼓里的局外人。而我因为我的“回避型”人格,主动选择了成为最后一个知情者。
我回到房间,林岚已经睡熟了。窗外的月光洒在她脸上,显得格外宁静。我躺在她身边,却毫无睡意。那些信里的字句,像烙印一样刻在我脑子里。
“……当年之事,是我之过。为兄不仁,听信谗言,将你赶出家门……父临终前,最念之人是你……”
“……我知你恨我,然血浓于水。若你收到此信,盼回一字……”
“……今日盼盼满月,若你能在,该有多好……”
我终于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把电视开到35分贝了。他或许不是真的耳背,他只是想用巨大的声响,来淹没心里那片叫“悔恨”的、无边无际的寂静。
第二章 车内的战场
周六一大早,天还没亮透,我们就出发了。我开着车,林岚坐在副驾,父母和盼盼在后座。一辆小小的SUV,塞进了三代人的心事,显得异常拥挤。
从我们居住的城市到扬州,全程高速大约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成了流动的战场。
起初还算平静。盼盼很兴奋,趴在车窗上看风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母亲拿出准备好的零食和水果,一会给盼盼递苹果,一会给父亲递水杯。父亲依旧沉默,但能看出他在努力地挺直腰板,像一个即将奔赴重要约会的年轻人。他标志性地擦了擦眼镜,然后戴上,望向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
第一个矛盾爆发在服务区。
林岚想去买杯咖啡提提神,母亲立刻拉住她:“买什么咖啡,浪费钱!我带了茶叶,保温杯里有热水,喝点热茶多好。”
林岚的表情僵了一下:“妈,我就想喝杯咖啡。”
“咖啡那东西喝了对身体不好,又苦又涩。”母亲开始念叨。
“妈,我就好这口。”林岚的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
我赶紧打断:“妈,没事,让她去吧,开车也辛苦。”我塞了五十块钱给林岚,“快去快回。”
林岚拿着钱走了,背影里透着一股压抑的怒火。我爸坐在车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是把头转向了另一边的窗外。
回到车上,车里的气氛明显冷了下来。林岚一口一口地喝着咖啡,像是喝什么解药。
盼盼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小声问:“爸爸,为什么奶奶和妈妈都不说话呀?”
我一时语塞,只能摸摸她的头:“大人在想事情呢。”
第二个矛盾,是关于路线。
按照导航,我们应该在下一个出口下高速。但父亲突然开口了:“顾明,别从这儿下。往前开,从瓜洲下。”
“爸,导航显示这里最近。”我看了眼屏幕。
“导航懂个屁!”他突然拔高了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命令口吻,“我说了,从瓜洲下!我要去看看润扬大桥。”
“爸,那要绕远二十多公里。”林岚忍不住了,“我们订的酒店在市区,从这儿下最方便。”
“绕远又怎么样?!”父亲的火气彻底上来了,他猛地一拍前排座椅的靠背,“我说了算还是导航说了算?我回趟家,看看风景,不行吗?!”
他的声音在狭小的车内空间里回响,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盼盼被吓得“哇”一声哭了出来。
“你吼什么!吓到孩子了!”林岚也火了,回头冲他喊道。
“我吼?我还没说你呢!从上车就拉着个脸,给我看脸色吗?不愿意来就别来!”
“爸!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了?我说错了吗?”
“好了!都别吵了!”我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嗓子。
车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盼盼压抑的抽泣声和发动机的嗡鸣。
(约4000字处)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父亲,他的脸因为激动而涨红,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梗着脖子,像一头好斗的公牛,但眼神里却闪过一丝孩子般的委屈。他低声嘶吼道:“人老了,连念旧都是一种错。”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地割着我的心。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打着转向灯,错过了导航提示的出口,朝着瓜洲的方向开去。
林岚气得把头扭向窗外,肩膀微微耸动。我知道她在哭。母亲抱着盼盼,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嘴里哼着我小时候听过的童谣,但那声音也带着一丝不易察arle的颤抖。
车子行驶在润扬大桥上,江面开阔,水天一色。这本该是壮丽的风景,此刻在我们眼里,却只剩下无尽的压抑。父亲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镜片后的眼睛里,情绪复杂。他是在怀念什么,还是在恐惧什么?
抵达扬州时,已经是下午。父亲没有让我们直接去酒店,而是指挥着我,把车开进了一条条狭窄的老巷。青砖黛瓦,石板小路,车子在里面穿行,像是闯入了一个陈旧的梦。
最后,车子停在了一栋破败的两层小楼前。木制的门窗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腐朽的木色。门口挂着一块“东关街xx号”的门牌,地址和那些信上的一模一样。
父亲推开车门,走了下去。他没有走近,只是远远地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栋房子,像一尊望乡的石像。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独。我们一家人坐在车里,谁也没有出声,仿佛一群闯入了别人悲欢的陌生人。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次来的不是扬州,而是父亲的心里。一座被他封闭了三十五年,早已荒草丛生、断壁残垣的心城。而我们,正站在城门口,不知是该进去,还是该转身离开。
第三章 母亲的坦白
在那栋老房子前,父亲站了足足有十分钟。他就那么站着,不说话,也不动,仿佛想把这三十五年的光阴都看穿。林岚在车里坐立不安,盼盼也早已失去了耐心,开始小声地哼唧。
“顾明,你下去看看吧。”母亲推了推我,声音里满是担忧。
我解开安全带,下了车。走到父亲身边,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味。他不知什么时候点了支烟,夹在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手指间。他很少抽烟。
“爸。”我叫了一声。
他像是才回过神来,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空洞。“……走吧,去酒店。”他掐灭了烟,扔进路边的垃圾桶,动作有些落寞。
去酒店的路上,车里的沉默比来时更加厚重。我把车开进酒店的地下车库,停好车。父亲和母亲带着盼盼先上去了。林岚坐在副驾,没有动。
“顾明,”她开口了,声音很疲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爸到底想干什么?”
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一阵抽痛。我的“回避”性格,不仅让我自己痛苦,也深深地伤害了我最亲近的人。我不能再瞒着她了。
“林岚,对不起。”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有些事,我可能……知道了。”
我把在行李箱里发现信件,以及那个叫“顾建军”的名字,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静静地听着,脸上的愤怒渐渐被震惊和复杂的情绪所取代。
“也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叔叔?”她喃喃地问。
“应该是。”
“所以这次来扬州,不是为了旅游,是为了……见他?”
我点点头。
林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怕麻烦,怕解释,怕面对她可能的质问和我们之间必然会因此产生的争吵。我的懦弱,让本可以共同分担的压力,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顾明,”她睁开眼,看着我,“有些事,你躲是躲不掉的。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也不是你爸一个人的。你总想着和稀泥,结果呢,泥没和成,所有人都陷进去了。”
她的话,一针见血。
我们回到酒店房间,父母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我让林岚和盼盼先休息,自己敲开了父母的房门。
开门的是母亲。她看到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父亲不在房间里。
“妈,我想跟您聊聊。”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我偷偷拍下的那封信的照片。
“顾建军,是谁?”我把手机递到她面前。
母亲看到那个名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扶住了床沿。“你……你怎么知道的?”
“爸的箱子里,有很多没寄出去的信。”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捂着嘴,无声地抽泣着,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压抑了几十年的秘密,一旦被揭开,所有的伪装和坚强都会在瞬间崩塌。
我扶着她在床边坐下。她哭了很久,才慢慢地平复下来。
“建军……是你叔叔,你爸唯一的亲弟弟。”她擦着眼泪,声音沙哑地开始讲述。
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悲剧。爷爷奶奶偏爱小儿子建军,觉得他聪明、有闯劲。而作为长子的父亲,则老实、木讷。兄弟俩的矛盾,在爷爷奶奶去世后分家产时彻底爆发。叔叔想拿家里唯一的祖宅去做生意,父亲坚决不同意,认为那是顾家的根。
“你爸那个犟脾气,你叔叔也年轻气盛。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最后你爸动手打了他,还说了一些狠话,让他滚,说顾家没有他这个不肖子孙。”
“你叔叔一气之下,就真的走了。刚开始几年还有零星的消息,后来就彻底断了联系。你爸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后悔。那几年,他偷偷写了好多信,但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他拉不下脸去打听,就那么一年一年地拖着。”
“你爷爷临终前,一直喊着建军的名字。你爸跪在床前,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从那以后,‘扬州’和‘建军’这两个词,就成了我们家的禁忌。”
母亲的叙述断断续续,充满了叹息和泪水。我终于明白了父亲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的逻辑。他执意要从瓜洲下高速,或许是因为当年叔叔就是从那个渡口坐船离开的。他站在老房子前久久不愿离去,是在凭吊一段回不去的兄弟情。
(约6000字处)
我听着母亲的哭诉,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拼命想逃离的故乡,却是父母一辈子也回不去的远方。那些我们早已不屑一顾的陈年旧事,却是他们背负了一生的枷锁。
“那这次来……”我轻声问。
“前段时间,你爸托扬州的一个远房亲戚,总算打听到了你叔叔的消息。他还在扬州,开了个小茶馆,日子……过得还行。”母亲的声音里有了一丝欣慰,“你爸就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回来一趟。他说,他想请你叔叔吃顿饭,当面跟他说声‘对不起’。这顿饭,他已经在心里准备了三十五年了。”
原来,那所谓的“在扬州的午餐”,竟是如此沉重。
“你爸联系他了吗?”
母亲摇摇头:“没有。你爸说,他没脸联系。他就想着,明天中午,去你叔叔的茶馆,就在那儿等。他来,就吃这顿饭。他不来……也算是了了自己一桩心愿。”
我走出父母的房间,感觉自己的双腿有些发软。秘密被揭开,但压力却更大了。明天的那顿午餐,将是一场豪赌,赌的是三十五年的隔阂与亲情,哪个更重。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林岚正靠在床头看书。她见我进来,放下了书。
“知道了?”
我点点头,在她身边坐下。
“我就知道。”她叹了口气,“你爸这个人,就是把所有的苦都自己扛,然后把所有的气都撒给最亲的人。”
“他也不容易。”我说。
“谁容易呢?”她反问,“他不容易,你妈不容易,你就不容易了?我就容易了?一家人,非要弄得跟猜谜语一样,有意思吗?”
她的语气很冲,我知道她在气头上。但我这次没有选择沉默和回避。
“林岚,对不起。”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不该让你一个人受委屈。以后……不会了。”
林岚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坦白地道歉。她眼圈红了,别过脸去,声音有些哽咽:“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之间的问题,和父亲与叔叔之间的问题一样,都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契机。而眼下,这个契机,就是明天那顿未知的午餐。
第四章 冷战与温情
秘密被揭开的那个晚上,我和林岚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地点不是在车里,而是在酒店房间那个不足十平米的封闭空间里。导火索是我的一句话:“明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支持爸。”
“支持?怎么支持?”林岚的情绪彻底爆发了,“顾明,你清醒一点!这不是我们支持不支持的问题!这是你爸三十多年前犯下的错,他凭什么要把我们所有人都绑上他的战车?盼盼做错了什么,要跟着我们在这里看脸色、挨训斥?我做错了什么,要放下工作,陪他来演这出苦情戏?”
“林岚,你小点声!”我急了,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隔壁的方向。
“小点声?你永远都是这句话!”她冷笑一声,站了起来,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顾明,我受够你了!你永远都在和稀泥,永远都在逃避!你爸强势,你妈软弱,你呢?你就是他们两个的结合体!你用你爸的方式来命令我,又用你妈的方式来要求我忍耐!你有没有问过我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上。因为她说的,全都是事实。我那个“维持和平”的核心缺陷,在她的控诉下,显得如此可笑和丑陋。
“我没有……”我的辩解苍白无力。
“你没有?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一件跟我们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在这里吵得面红耳赤?你爸想赎罪,那是他的事!他不应该把他的罪恶感,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不公平!”
“那是我爸!”我终于也吼了出来,“他是我爸!他不好过,我能好过吗?”
“所以你就让我陪着你一起不好过?”她也寸步不让。
情绪越激烈,句子越短。
“你讲点理!”
“理?家里没理!”
“你不可理喻!”
“对!我就是!”
争吵在我的摔门而出中戛然而生。我冲到酒店的楼梯间,一个更小的密闭空间。我靠着冰冷的墙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烟瘾前所未有地涌了上来。我摸遍了口袋,却什么也没找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我推开楼梯间的门,走廊里静悄悄的。我回到房间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却迟迟没有勇气推开。
我最终还是没有回房间,而是去了酒店大堂的沙发上,蜷缩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被保洁阿姨的吸尘器声音吵醒。脖子僵硬,浑身酸痛。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房间,林岚已经起来了,正坐在梳妆台前,但没有化妆,只是静静地坐着。盼盼还在熟睡。
我以为她会继续给我冷脸,但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床头柜。
那里放着一杯水,还是温的。旁边,是我常吃的那瓶胃药。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拿起水杯,一口气喝光了。然后走到她身后,看着镜子里的她。她很憔ें悴,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从衣柜里拿出一条薄毯,轻轻地披在了她的肩上。她从镜子里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
这无声的关怀,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我们都太累了,累到没有力气再去争吵。冷战还在继续,但那层坚冰之下,似乎有了一丝暖流在悄悄涌动。
我们都知道,对方是自己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唯一的同盟。
(约7500字处)
吃早饭的时候,气氛依旧尴尬。父亲大概也知道我们昨晚吵架了,一直低着头喝粥,没说话。
突然,林岚开口了。她是对着盼盼说的:“盼盼,吃完饭,妈妈带你去瘦西湖玩好不好?我们不等爷爷了。”
我心里一惊。我知道,这是她最后的通牒。
父亲拿筷子的手僵住了。他抬起头,看着林岚,眼神里是震惊,是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哀求。
我正要开口打圆场,林岚却又说话了。她看着我,眼神异常平静,但说出的话却字字扎心。
(约8000字处)
“过日子,”她轻声说,像是在对我,又像是在对自己说,“就是把心熬成药,苦了自己,才能治家人的病。”
这句话,让我所有的辩解都堵在了喉咙里。是啊,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熬着这副名叫“家庭”的苦药。
最终,还是父亲先妥协了。他放下筷子,声音沙哑地说:“……林岚,爸对不起你。这件事,是爸不好。”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对不起”。
林岚的眼圈瞬间就红了。她别过脸去,用力地吞咽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爸,我没有怪你。我只是……只是心疼顾明,也心疼盼盼。”
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就这样消弭于无形。我知道,是林岚的退让,也是父亲的妥协,更是我们之间那份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存在的亲情,在关键时刻拉了我们一把。
吃完早饭,我们没有去瘦西湖。我们一起,陪着父亲,去赴那场迟到了三十五年的午宴。
第五章 等不来的午餐
叔叔的茶馆,名叫“晚香”。
这是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坐落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青砖铺地,门口挂着两盏古朴的灯笼。推门进去,一阵淡淡的茶香混合着檀香的味道扑面而来。
茶馆里客人不多,三三两两地坐着,低声细语。一个穿着棉麻对襟衫,看起来比我父亲年轻不了多少的男人,正站在柜台后,慢悠悠地擦拭着茶具。他的眉眼,和那张老照片上的“建军”,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多了几分岁月的风霜。
他就是我的叔叔,顾建军。
父亲在门口站定了,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脱下外套,露出里面崭新的白衬衫,那是母亲特意为他准备的。他深吸了一口气,标志性地扶了扶眼镜,然后迈步走了进去。
我们跟在他身后。
叔叔听见门口的风铃响,抬起头。当他的目光和父亲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时间仿佛静止了。
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错愕,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疏离。他擦拭茶具的动作停了下来。
父亲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沙哑地吐出两个字:“……建军。”
叔叔没有回应。他只是看着我们,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到母亲身上,再到我、林岚,最后落在盼盼的脸上。他的眼神柔和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几位?喝点什么?”他开口了,声音平淡得像在招呼最普通的客人。
父亲的身体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他。我能感觉到,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我们……我们想找个位置,吃顿饭。”我替父亲。
“这里只喝茶,不吃饭。”叔叔的语气依旧冷淡。
“我们……是你哥哥。”母亲忍不住开口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叔叔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是一个冷笑。“我没有哥哥。”
这句话,像一把最锋利的刀,直直地插进了父亲的心脏。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和他的衬衫一样白。他张着嘴,大口地喘着气,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走吧。”叔叔别过脸去,不再看我们,重新拿起一块茶饼,用茶针撬动着,“我这里要做生意了。”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残忍的拒绝。
我们被“请”出了茶馆。站在巷子里,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父亲靠在墙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灵魂,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
“爸,我们先回去吧。”我劝道。
他摇摇头,固执地走到茶馆对面的一个石阶上,坐了下来。“我等。”
“等?”
“我等他关门。”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像从胸腔里挤出来一样,“他说过,他饿了的时候,最想吃妈做的狮子头。我去菜场买菜,回去做给他吃。”
我的视线瞬间模糊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在巷子里,陪着他等。林an带着盼盼在附近的小店里逛,我和母亲陪着父亲。他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坐着,像一尊雕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茶馆里的客人来了又走,叔叔一直在柜台后忙碌着,他一次也没有朝我们这边看过。
太阳从正午,慢慢地偏西。
(约10000字处)
母亲看着父亲的背影,眼泪又流了下来。她喃喃地说:“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等不到,也是一辈子。”
一直等到傍晚,茶馆的灯笼亮了起来,叔叔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他拉下木制的门板,准备关门。
父亲猛地站了起来,快步走了过去。
“建军!”他叫住了他。
叔叔的身体僵住了,但没有回头。
“我……我给你做了狮子头。”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和祈求,“就在酒店,你……你跟我回去吃一口,就一口,行吗?”
叔叔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我早就不爱吃那玩意儿了。”他冷冷地丢下这句话,然后拉上最后一扇门板,上了锁,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巷子的深处。
父亲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那一天,我们最终还是吃了一顿“在扬州的午餐”。地点是在酒店的房间里,桌上摆着一份几乎没怎么动的、早已冷掉的红烧狮子头。
没有人说话。电视机没有开,房间里安静得可怕。这种安静,比35分贝的喧嚣更让人窒息。
父亲坐在桌边,一口一口地,把那盘冷掉的狮子头,全都吃了下去。他吃得很慢,很用力,像是在咀嚼他那三十五年无法下咽的悔恨。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不再是那个专制、固执的父亲。他只是一个犯了错,并且用半生来惩罚自己的,可怜的老人。
第六章 阳台的黎明
从扬州回来的路上,父亲彻底沉默了。
他不再指挥我该走哪条路,也不再抱怨窗外的风景。他只是靠在后座,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但我知道,他醒着。他那微微颤抖的眼睑,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那顿没有等到客人的午餐,像一块巨石,压垮了他所有的倔强和伪装。
回到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都没出来。晚饭时,我敲开他的门,他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那副擦得锃亮的老花镜,却没有戴,只是怔怔地看着窗外。
“爸,吃饭了。”
他回过头,眼神很茫然。那是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一种近似于孩童般的无助。
“我不饿。”他说。
晚饭桌上,气氛沉闷。电视机破天荒地没有打开。那熟悉的35分贝消失了,整个家安静得让人心慌。林岚默默地给盼盼夹菜,母亲则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饭后,我走进父亲的房间。他还是那个姿势。
“爸,”我搬了张椅子,在他身边坐下,“跟我说说叔叔吧。小时候的事。”
他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点光。
他没有说那场决裂,也没有说那些悔恨。他说的,都是些很小很小的事。说他们小时候怎么一起去河里摸鱼,怎么偷邻居家的石榴被追着打;说叔叔从小就聪明,字写得比他好,算盘也打得比他快;说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把自己的棉手套给了手生了冻疮的弟弟,自己却冻得满手是伤。
他讲得很慢,声音很低,像是在回忆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
我静静地听着。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第一次如此心平气和地交谈。没有说教,没有争吵,只有一个老人在对他的儿子,袒露自己内心最柔软,也最疼痛的部分。
(约12000字处)
我忽然意识到,父亲从未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男人,他只是用一生向我展示,一个犯过错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他的固执,他的沉默,他的悔恨,他的笨拙的爱,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完美,但却无比真实的父亲形象。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扬州号码。我走到阳台,按下了接听键。
“喂,你好。”
“……你好。”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沙哑,也有些迟疑,“请问,是顾兆祥的儿子,顾明吗?”
我心里一震:“我是。您是……”
“我是顾建军。”
我的呼吸瞬间停止了。
“我……我看到你们了。”叔叔的声音很低沉,“那天,你们在茶馆对面的巷口。我……我看到了。”
“那您为什么……”
“我不敢。”他苦笑一声,“三十五年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见他。我怕我一看到他,就会哭。我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了,不想在他面前丢脸。”
“他……他很想您。”
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我知道。我哥那个人,就是头犟驴。我知道他后悔了。”他顿了顿,继续说,“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只是……我还没想好怎么原谅我自己。当年,如果我不那么冲动,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样。”
原来,这三十五年的枷锁,锁住的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
“我明天要去你们那边办点事。”叔叔突然说,“我想见你一面。就你一个。有些东西,我想让你转交给他。”
第二天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按照约定,来到了小区附近的公园。
叔叔已经到了。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站在湖边,背影看起来和父亲一样,有些佝偻。
他见我来了,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沧桑,也有释然。
我们没有说太多话,只是在公园里慢慢地走着。他跟我讲了些他这些年的经历,结了婚,又离了,没有孩子,守着那个小茶馆,过得平淡也安稳。
“他……身体还好吗?”他问。
“老毛病了,高血压。耳朵也不太好。”
他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东西,递给我。“这个,你帮我交给他。”
“这是什么?”
“他会知道的。”他说,“你告诉他,当年的事,都过去了。让他……别再折磨自己了。”
告别了叔叔,我拿着那个小小的手帕包,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回到家,推开门,看见父亲正站在阳台上。他穿着单薄的睡衣,望着远处刚刚升起的太阳。清晨六点的微光,给他花白的头发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似乎一夜没睡。
我走到他身后。
“爸。”
他回过头,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手里的东西。
我慢慢地摊开手帕,里面是一颗用红线穿着的、已经磨得非常光滑的石子。石子上,用稚嫩的笔触,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祥、军。
父亲的眼睛,瞬间就红了。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剧烈地颤抖,伸出的手,也抖得不成样子。那是我在河边捡到的,送给他的……他喃喃自语,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用一辈子来演绎“固执”的男人,此刻像个孩子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我知道,这颗小小的石子,解开的是他心里那个锁了三十五年的死结。
我张开嘴,想把叔叔的话告诉他。
“爸,叔叔他……”
我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已经伸出手,颤抖着,慢慢地、慢慢地,朝着那颗石子碰了过去。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一滴浑浊的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滚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