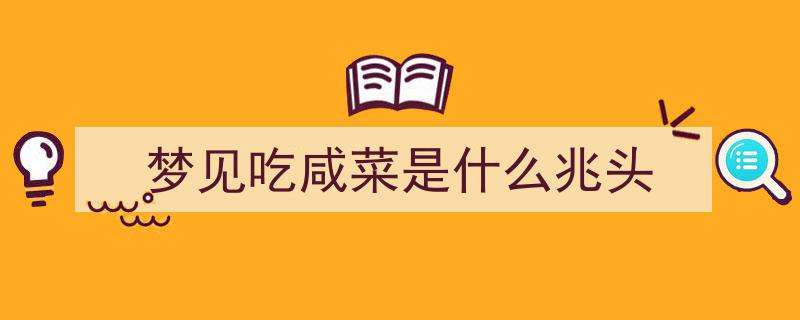咸菜与苹果
"咸菜蘸米饭,吃得真香啊!"我笑着对堂哥说,嘴里咀嚼着那一口略带咸涩的青菜。
这是1988年的高中食堂,空气里弥漫着食物的混合气味,夹杂着青春期少年特有的汗臭和朝气。
堂哥盯着我碗里那几筷子从家里带来的咸菜,眉毛微微上扬,嘴角下撇,仿佛我碗里装的不是咸菜,而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就吃这个?"他问,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几个同学都转过头来。
我点点头,继续扒拉着我的饭菜,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享受这顿简单的午餐。
堂哥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润的苹果,递到我面前,眼里带着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似是怜悯,又像是某种优越感。
"吃这个吧,咸菜吃多了伤身体。"他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不愿承认的善意。
我没接,低头继续吃我的咸菜。
那时候,家里条件艰难,父亲刚从纺织厂下岗,每天起早贪黑去建筑工地当小工,晚上回来时,总是一身的灰尘和疲惫。
母亲小腿静脉曲张,站不了长时间,却还要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些针头线脑,补贴家用。
每月的生活费挤得我喘不过气来,咸菜就成了我最忠实的"伙伴"。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口头禅,但我知道,这世上的福与难,从来就不是平均分配的。
堂哥的父亲——我的叔叔,在县里供销社当科长,手里有实权;婶婶是县医院的护士長,穿着白大褂走路带风,在那个"白衣天使"备受尊崇的年代,简直就是半个神仙。
我和堂哥虽是同龄人,却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每天放学回家,总能看见母亲佝偻着背在灶台前忙碌,腌咸菜的大缸就放在厨房角落。
"腌得咋样?"我会凑过去问。
"今年的白菜老香了,腌出来的咸菜准好吃。"母亲总是这么,脸上的皱纹里藏着朴实的喜悦。
"孩子,咸菜蘸饭也有滋味,你爹以前读书时就这么过来的。"母亲常这样宽慰我,"清苦日子熬出来的人,心里头都有本账。"

相比之下,堂哥家境优渥,家里的电视机、冰箱都是最早一批添置的,我们村的人还专门去他家参观过这些"新鲜玩意儿"。
有一次,我去他家送东西,偷瞄了一眼他家的餐桌: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水果盘。
那顿饭的香气,我记了很久,有时夜里做梦,还能梦到那股子肉香。
"你吃过糖醋排骨没?"堂哥曾在课间问我。
我摇摇头,不好意思承认那是我从未尝过的味道。
"那你真是太亏了,"他咂咂嘴,"那滋味,酸酸甜甜的,一口下去,骨头都想嚼碎了吞进肚子里。"
他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含着我不懂的幸福。
我那时心里酸溜溜的,不是因为糖醋排骨的滋味,而是因为自己的不如人。
高二那年冬天的一个雨夜,天地间漆黑一片,雨点像是被人使劲甩出来的,啪啪地打在屋顶上,声音大得吓人。
母亲突然疼得直不起腰,冷汗涔涔,面色惨白。
"肚子疼,肚子疼得厉害。"母亲咬着牙说,额头上的青筋都凸了出来。
父亲出门打零工还没回来,我二话没说,背起母亲冲进雨里。
雨水打在脸上,冰凉刺骨,但背上母亲的重量却让我觉得温暖而沉重。
"没事,娘,我背你去医院,很快就到。"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在泥泞的路上小心前行。
村口的路灯下,我看见了几个值夜的村民。
"小子,这是咋了?"大伯问。
"我娘肚子疼,得去医院。"我气喘吁吁地。
"要不我找个三轮车送你们?"大伯说。
我摇摇头:"来不及了,我背着快。"
十八岁的身体,有使不完的力气和永远不怕吃苦的勇气。
那天,我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了值班的婶婶,她穿着洁白的护士服,手里拿着病历本,见到我们的狼狈样子,先是一愣,随后匆匆走过来。

"这是怎么了?"她问,眼神在我和母亲之间徘徊。
"腹痛,很严重。"我简短地说,没有多余的解释。
婶婶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帮我们安排了病床,还找来医生给母亲检查。
"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手术。"医生说,"交三百块钱押金。"
三百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掏遍全身口袋,只有五十多块钱,是这个月的全部生活费。
"我去找人借。"我对婶婶说,心里却没底,不知道该找谁借这么一大笔钱。
婶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先做手术吧,钱的事情后面再说。"
她在表格上签了字,算是为我们担保。
手术很顺利,母亲转危为安。
第二天一早,父亲赶到医院,眼睛里布满血丝,看起来一夜没合眼。
"手术费用我来付。"他说,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许久的零钱和皱巴巴的纸币。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天晚上跑遍了全村,东家借十块,西家借二十块,凑齐了手术费。
堂哥来医院看望时,带了一袋橘子和一盒饼干,看起来心情不错。
"你妈没事吧?"他问,语气里带着一种轻飘飘的关心。
"没事了,谢谢。"我说。
他环顾病房,皱了皱眉头,似乎对这简陋的环境有些不适应。
"我娘说了,有啥困难尽管说。"他说,"咱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他临走时,又忍不住嘲笑我:"咸菜命啊,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没回嘴,只是握紧了母亲的手。
母亲虚弱地对我笑笑:"他不是故意的,年轻人嘴上没把门的。"
我知道,母亲是在为堂哥开脱,但我心里却默默在想:不,他就是故意的。
出院那天,婶婶帮我们办了减免手续,少付了一部分费用。
"老王家的孩子真懂事。"医院里的人这样评价我。
回家的路上,母亲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儿子,娘欠你的。"

我鼻子一酸,差点落泪:"您别这么说,您和爹把我养这么大,我啥都没做。"
家里的日子依旧艰难,但我的学习却从未落下。
高考那年,我把自己关在县图书馆里,连寒暑假都没回家。
每天天不亮就去排队,晚上闭馆才离开,吃的还是从家里带的咸菜和馒头。
那种饥饿感和对知识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竟成了一种特别的滋味,像极了家里腌的老咸菜,越咸越有味道。
图书馆的管理员老李见我来得早走得晚,时常会给我留个靠窗的好位置。
"娃,你这么拼命读书,为啥呀?"他有一天问我。
"为了改变命运。"我脱口而出。
老李笑了:"好志氣!年轻人就该这样。"
与此同时,堂哥却过着截然不同的高三生活。
听同学说,他常常逃课去镇上的游戏厅,甚至学会了抽烟喝酒。
叔叔为此找过他好几次,但堂哥满不在乎:"反正有关系,考不上还能走后门。"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只是笑笑,没有评判。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我选择了咸菜和书本,他选择了游戏和酒精。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全村人都轰动了。
父亲破天荒地喝了二两白酒,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着泪光:"我儿子争气啊!"
母亲偷偷抹泪,嘴里念叨着:"值了,这些年的苦没白吃。"
邻居们纷纷上门道贺,有的带着鸡蛋,有的带着自家种的蔬菜,还有人直接塞给我几张皱巴巴的钱币:"娃,上大学花钱,这是叔的一点心意。"
我每次都想推辞,却被父亲拦住:"人家是真心实意的,不收反倒伤感情。"
叔叔家却格外安静,没有喜庆,也没有祝贺。
后来听说,堂哥落榜了,连本科线都没过。
这个消息传来时,我并没有想象中的痛快,反而有些惆怅。
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里,我和堂哥能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兄弟,而不是被家境和命运推向两个极端的陌生人。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叔叔动用关系,托人找了门路,最终堂哥被本地一所专科学校的会计系录取了。
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总算有了个去处。
从此,两家的往来少了。
我背起行囊去了北京,那座让我既向往又害怕的大城市。
临行前,母亲塞给我一罐自己腌的咸菜:"带上,想家的时候尝一口。"
那个装咸菜的罐子,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个瓷罐,上面还绘着青花。
在北大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艰难得多。
来自农村的我,和那些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有着明显的差距——不仅是知识面,还有见识、气质和自信。
我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穿着土气,身上总有一股咸菜的味道——至少我自己这么觉得。
第一个学期,我几乎不敢在课堂上发言,生怕被人嘲笑。
直到有一次,文学理论课上,教授提问一个关于《红楼梦》的问题,全班鸦雀无声。
我鼓起勇气举手,用我那不标准的普通话了问题。
教授听完,眼睛一亮:"说得好!这位同学思考得很深入啊。"
从那以后,我渐渐找回了自信,不再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自卑。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给人家做家教,周末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假期在餐馆当服务员,攒钱补贴家用,从不跟家里要一分钱。
毕业那年,我拿到了国企的offer,薪资待遇在同届毕业生中名列前茅。
十年光阴如水,我在一家国企步步高升,而堂哥却还在啃老,几次创业都失败了。
先是开了个小超市,因为经营不善,半年就关门了;后来又做服装生意,赶上了行业低谷,亏了不少;再后来听说他去做传销,被公安机关教育了一番……
每次失败,都是叔叔婶婶出面摆平,掏钱填窟窿。
有一次回老家,听村里人说起堂哥,不由得感慨:"你说这人怎么搞的,家里条件那么好,咋就做啥啥不成呢?"

我只是笑笑,没有评价。
每个人的命运,也许早已在某个不经意的选择中埋下伏笔。
那个曾经递给我苹果的少年,如今成了一个沉浸在父母光环下无法自立的中年人。
而我,那个只能靠咸菜度日的穷小子,却在岁月的磨砺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去年冬天,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突发脑梗,我从北京连夜赶回。
老家的冬天特别冷,但医院的暖气却开得很足,病房里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病房里只有母亲一人守着,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又深了几分,头发已全白。
"爹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
"医生说没大碍,就是需要静养。"母亲疲惫地说,"你回来就好,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问起堂哥家,母亲摇摇头:"他们早搬到省城去了,说是做生意,也不常回来。"
言语间,有一丝我读得懂的失落。
血缘关系再亲近,也抵不过现实生活的疏远。
那天晚上,我守在父亲床前,看着他沧桑的面容和花白的头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记忆中高大威猛的父亲,如今已是风烛残年。
父亲醒来看见我,眼里有光:"是诚诚回来了?"
"是我,爹。"我握住他的手,感受着那布满老茧的粗糙触感。
"你工作别太累,放下手头的事赶回来,爹心里过意不去。"父亲虚弱地说。
"说啥呢,您和娘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这点算啥?"我哽咽道。
父亲虚弱地拉着我的手说:"娃啊,人生就像咸菜,越咸越有滋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当年堂哥递给我的那个苹果里包含的情绪——那是怜悯,也是一种隔阂。
而如今,我和堂哥的人生轨迹已经渐行渐远,宛如一道无法跨越的河流。
回到北京后,我意外收到了堂哥的微信好友申请。
头像是一张精修过的自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表弟,听说伯父住院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他问。

"已经出院了,在家静养。"我简短地回复。
"那就好,那就好。"他说,然后话锋一转,"对了,表弟,你现在在国企当领导了吧?我有个项目想找你聊聊,很有前景的。"
我看着手机屏幕,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
时间真是最好的过滤器,它会无情地筛选出一个人的本质和价值。
那个曾经递给我苹果的少年,如今只记得我"在国企当领导"这一点;而我,却始终记得他眼中的怜悯和嘲讽。
"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很忙,等有空再聊吧。"我最终这样回复,然后将手机放到一旁。
窗外飘起了雪,北京的冬天来得比家乡更晚一些,但同样寒冷刺骨。
我打开冰箱,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食材和饮料,还有几罐母亲亲手腌制的咸菜。
我取出一罐,打开盖子,那熟悉的咸香立刻溢满了整个厨房。
我咬了一口咸菜,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滋味在舌尖绽放,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那个只有咸菜相伴的少年时代。
我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想起了那个夏天的咸菜,那个冬天的苹果,还有那个雨夜里沉重的背影。
咸菜的滋味,是苦尽甘来;苹果的滋味,是外甜内虚。
人生百味,终究要自己品尝。
若干年后,我接到了堂哥车祸去世的消息。
那一刻,我的心情格外复杂,既有悲伤,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葬礼上,我见到了憔悴不堪的叔叔婶婶,他们一夜之间似乎老了十岁。
"孩子,你表哥生前一直很敬佩你。"婶婶拉着我的手说,"他常说,当年要是像你那样努力,现在也不会这样。"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心里却在想: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儿时的家。
屋子还是那个屋子,墙角的咸菜缸也还在那里,只是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父母搬去了城里,和我一起住,这老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我站在厨房里,仿佛看见了年少时的自己,正蹲在咸菜缸旁,津津有味地吃着那一口咸菜。
苦咸的滋味,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它塑造了我,也成就了我。
如今,我可以吃到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住最豪华的酒店,去最遥远的国度旅行。
但在我心底,永远珍藏着那个只能吃咸菜的少年,和他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母亲常说:"咸菜虽咸,却能防腐保鲜;日子虽苦,却能磨炼意志。"
如今,我终于读懂了这句话的真谛。
人生如咸菜,越咸越有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