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人,常州之行三问不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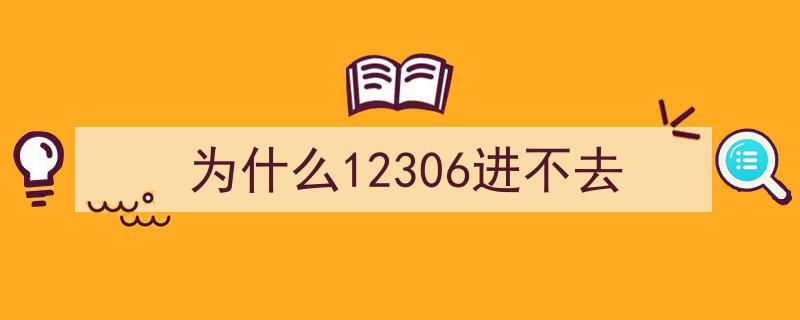
哈哈,常理解!安徽和江苏山水相连,文化习俗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确实有些地方会让老乡们感到些微不同。您去常州这三个疑问,非常具体,我来试着帮您解答一下,希望能让您释疑:
1. "关于“常州”这个名字的疑问?"
这个可能和您对江苏其他城市,比如南京、苏州、扬州这些带“江”字的城市有所联想有关。江苏因地处长江下游而得名。
常州虽然也位于长江边(常州地处长江下游,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市),但它的名字里没有“江”字。关于常州名字的由来,最普遍和流传较广的说法是:
"“常”":取自“常乐”、“长治久安”之意,寄托了人们希望此地能够永远安宁、繁荣的美好愿望。
"“州”":古代指水边弯曲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区域、单位的名称。常州古称“晋陵”,是古代的州治所在地之一。
所以,“常州”这个名字更多是寄寓了美好的愿景,而不是直接描述它的地理位置特征(虽然它确实临江)。江苏内部城市名称的由来也各有特色,并非都带“江”字,比如无锡、南通、盐城等也不带“江”字。
2. "关于常州话(常州方言)的疑问?"
相关内容:
我是安徽人,去了趟江苏常州,有三个疑问就是不明白,忍不住问下。
【引子】
火车进入江苏境内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就变了。不再是皖北平原那种一望无际的、带着点土黄色的粗犷,而是被切割得整整齐齐的、水汽氤氲的绿。那种绿,精细得像绣娘手里的丝线,一针一针,密密地缝在你看得见的每一寸土地上。
我叫陈默,沉默的默。我姐叫陈静,安静的静。我爸妈给我们取这名字,是希望我们这辈子能安安稳稳,少惹事端。我在合肥一家国企做技术员,日子不好不坏,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我姐陈静,五年前嫁到了常州。
姐夫李浩,是她大学同学,常州本地人。当年我爸妈一百个不同意,说嫁那么远,受了欺负娘家都赶不及。我姐跪在堂屋里,只说一句:“这辈子,就是他了。”
我爸气得把烟杆都摔了,最后还是我妈流着泪,一边给她收拾行李,一边往她箱子底下塞钱,嘴里念叨着:“到了那边,别省,别让人家看轻了。”
五年,我们只在过年时见一见。每次回来,姐姐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给我们带一堆包装精美的常州特产,说李浩对她怎么怎么好,公婆怎么怎么开明,常州发展怎么怎么快。我们全家都觉得,她赌对了。
直到上个星期,她半夜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很安静,只能听到她压抑着的、细微的抽泣声。我心里一紧,连问怎么了。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然后,她用一种几乎快要碎掉的声音说:“哥,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我连夜请了假,买了最早一班去常州的火车。
坐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我想了一路。我想起她每次回家,虽然笑着,但眼角总有一丝我读不懂的疲惫。我想起姐夫李浩,永远客气周到,但那客气里,总隔着一层薄薄的、捅不破的膜。我想起我五岁的小外甥女瑶瑶,漂亮得像个洋娃娃,但总比同龄的孩子安静一些。
我此行揣着三个巨大的疑问,像三块石头压在心口。这三个疑问,是我这几年零零碎碎从我姐偶尔的电话里,从我妈忧心忡忡的转述里,拼凑出来的,关于她“幸福生活”的全部不解。
第一,为什么常州的女婿,每个月给我姐三千块零花钱,她还总是哭着说日子过不下去?
第二,为什么我外甥女在学校受了欺夫,我姐夫不去找对方家长,反而带孩子去吃了顿肯德基,还说这是“格局”?
第三,为什么我爸妈在老家省吃俭用,用土灶熏出来的香肠腊肉,大老远寄过去,我姐夫转手就送了邻居,还笑着跟我姐说,这叫“人情社会”?
火车到站的提示音响起,我拎着行李走出车站。常州的空气湿润而温暖,跟合肥的干爽完全不同。我姐和姐夫就站在出站口,远远地朝我挥手。
我姐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眼下的乌青有点遮不住。姐夫李浩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戴着金边眼镜,斯文儒雅。他热情地接过我的行李,笑着说:“大舅子,一路辛苦了。走,回家,你姐念叨你好几天了。”
我看着他们,笑了笑,心里的石头,却一块也没落下去。
【第一章:三千块的围城】
李浩的家在常州一个挺新的小区,电梯房,一百二十多平,装修是那种简约的北欧风,干净、敞亮。客厅的阳台上种满了花花草草,看得出我姐的精心打理。
晚饭是四菜一汤,红烧排骨、清蒸鲈鱼、番茄炒蛋、一盘青菜,都是我爱吃的。我姐不停地给我夹菜,李浩则陪我喝着酒,聊着合肥和常州两地的发展,聊着我的工作。气氛看上去热烈而融洽。
“哥,你多吃点,这鲈鱼新鲜,李浩特地去菜场挑的。”我姐笑着说,眼角的笑意却像浮在水上的油花,漾开,又很快散去。
“姐夫有心了。”我端起酒杯。
李浩摆摆手,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一条线:“一家人,说这个就见外了。陈静总说你工作忙,难得来一次,必须招待好。”
他说话永远这样,滴水不漏,让你觉得亲切,又让你觉得这份亲切是标准化的,可以复制给任何人。
饭后,李浩去书房打电话,似乎在谈工作。我姐在厨房洗碗,我走过去想帮忙。
“去去去,坐着看电视去,哪有让客人洗碗的。”她把我往外推。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她曾经也是家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公主,现在却熟练地处理着油腻的碗筷。她的标志性小动作没变,紧张或者有心事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右边的耳垂。此刻,她的手就在耳垂上捏了一下。
“姐,”我轻声问,“钱……够花吗?”
她的背影僵了一下。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着,掩盖了那一瞬间的凝滞。
“够啊,怎么不够。”她转过头,对我笑了笑,“李浩每个月给我三千呢,我又不上班,瑶瑶上幼儿园也花不了多少,够用了。”
我看着她,没说话。这笑容,和我妈每次跟我说“我身体好着呢,别担心”时一模一样。
晚上我睡在次卧,房间很干净,床单被套都散发着阳光的味道。可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主卧隐隐传来争吵声,很压抑,像两只困兽在低吼。
“……我哥都看出来了!你让我怎么说?”是我姐的声音,带着哭腔。
“看出来又怎么样?难道要我满世界嚷嚷我生意出了问题吗?你让我爸妈怎么看我?让你哥怎么看我?”李浩的声音,不再是白天的温文尔雅,充满了烦躁和疲惫。
“可我苦啊!我真的苦啊李浩!三千块,物业费一千,瑶瑶的兴趣班一千五,水电煤气买菜……我每天睁开眼就是算账!我连一件新衣服都不敢买!我哥来了,我还是穿前年的裙子……”
后面的话,被一阵更低的呜咽代替。
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凉了。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吗?不是她贪心,而是那三千块,在这座光鲜的城市里,被一张叫做“生活”的网,过滤得一滴不剩。
第二天一早,我姐顶着红肿的眼睛给我做早饭。李浩也起来了,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又挂上那副标准笑容:“大舅子起这么早?昨晚睡得好吗?”
我看着他,也看着我姐。他们像两个默契的演员,在天亮之后,又迅速地戴上了幸福的面具。
我忽然觉得,这个家就像一个精美的玻璃罩,外面看着流光溢彩,里面的人,却快要窒息。
吃完早饭,我借口出去逛逛,一个人在小区里走。我看到穿着体面的主妇们,讨论着新买的包,孩子新报的马术课。我走到小区门口的超市,看了一眼物价,一把青菜五块,一斤猪肉三十。
我终于明白,我姐那句“日子过不下去”,不是矫情,是实话。那三千块,是李浩身为一个男人最后的体面,也是套在我姐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第二章:“格局”的代价】
关于第二个疑问的答案,是在我来的第三天下午揭晓的。
那天下午,我姐去参加一个社区烘焙课,李浩公司有事,我去幼儿园接瑶瑶。五岁的小外甥女像个小天使,皮肤白得发光,眼睛又大又亮。可我接到她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拽着我的衣角,不说话。
我蹲下来,才看到她白嫩的胳膊上有一道清晰的牙印,已经泛紫了。
我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这在老家,是天大的事。
“瑶瑶,谁咬的?告诉舅舅!”
瑶瑶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瘪着嘴,小声说:“是……是浩浩,他抢我的小红花。”
“老师呢?老师不管吗?”我心疼得发紧。
“老师批评他了……可是他放学还推我。”
我拉着瑶瑶,掉头就要回幼儿园找老师,找那个叫浩浩的家长。我陈默的亲外甥女,不能就这么白白受了欺负。
刚走到幼儿园门口,李浩的车就到了。他摇下车窗,看到我们,愣了一下:“怎么又回来了?”
我把瑶瑶的胳膊伸给他看,压着火说:“瑶瑶被同学欺负了,我得去找他们家长说道说道。这叫什么事!”
李浩的眉头皱了起来。他下车,看了看瑶瑶的伤口,又摸了摸她的头。我以为他会跟我一样愤怒,但他没有。他只是平静地对我说:“哥,先上车吧。”
我愣住了:“上车?这事就这么算了?”
“先上车,我跟瑶瑶聊聊。”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车里,我憋着一肚子火。瑶瑶坐在后座,还在小声抽泣。我以为李浩会批评她为什么不还手,或者安慰她别怕,爸爸去给你报仇。
结果,李浩从后视镜里看着女儿,说了一句让我差点跳起来的话。
“瑶瑶,想不想吃肯德基?”
瑶瑶的哭声停了,点了点头。
我忍不住了:“李浩!现在是吃肯德基的时候吗?孩子受了欺负,你不去解决问题,你带她去吃东西?”
李浩没有看我,一边打着方向盘,一边说:“哥,你觉得,我现在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大吵一架,甚至打一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
“那不然呢?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我反问。
“结果呢?”李浩说,“结果就是两个孩子成为敌人,两个家庭成为敌人。瑶瑶以后在幼儿园会被孤立,那个男孩会变本加厉地欺负她,因为他的父母会觉得是我们让他们丢了脸。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噎住了。
车停在肯德基门口。李浩抱着瑶瑶,点了一个全家桶。他没有再跟我争论,只是把瑶瑶放在座位上,抽出一张纸巾,仔仔细细地擦着她脸上的泪痕。
他看着女儿的眼睛,非常认真地说:“瑶瑶,爸爸知道你委屈。但是你要记住,被人欺负,哭和告状是没用的。你要做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那个浩浩为什么能欺负你?因为他比你高,比你壮。那你就要多吃饭,多锻炼,长得比他更高,跑得比他更快。”
他顿了顿,把一个鸡腿递给瑶瑶:“第二,你要比他更聪明。他抢你的小红花,你可以告诉老师,这是对的。但老师批评完他,他还会找你麻烦。下次,你可以试着跟他说,‘这朵小红花我送给你,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朋友是不会互相欺负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李浩的声音很轻,却很有力量,“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甚至欺负你。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也不可能跟每一个人去计较。你要把你的力气,用在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变得更好上。这叫‘格局’。懂吗?”
瑶瑶似懂非懂地啃着鸡腿,点了点头。
我坐在对面,看着这对父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脑子里回想着老家处理这种事的方式:大人们冲到学校,唾沫横飞地对骂,最后扭打在一起,孩子们在旁边吓得哇哇大哭。最后的结果,就像李浩说的,仇恨的种子,就那么种下了。
李浩的方法,我还是不能完全认同,总觉得憋屈。但他说的“格局”两个字,却像一颗钉子,钉在了我的心里。
他不是不在乎女儿,他是在用一种我完全不理解的方式,教她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更聪明地保护自己。
吃完肯德基,回家的路上,李浩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语气又变回了那种客气而疏离的调调:“王总,您好您好……对,方案我发您邮箱了……好的好的,您先忙。”
挂了电话,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习惯性地用手指敲了敲方向盘。那个小动作,我以前以为是得意,现在看来,全是焦虑。
我忽然明白了。他不去学校闹,或许不全是为了“格局”。更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闹。他的人生,已经被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填满了,比如那个“王总”,比如那个他没说出口的生意。
孩子的委屈,在他的世界里,只能用一顿肯德C来安抚和补偿。这是一种成年人的无奈,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妥协。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真实得让人心疼。
【第三章:一包腊肠的人情】
压在我心口的第三块石头,也是最重的一块,在我来的第五天,被搬开了。但搬开的方式,几乎将我击碎。
那天,快递员送来一个巨大的泡沫箱,上面用马克笔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家的地址。是我妈寄来的。每年入冬,我妈都会用老家的土猪肉,混着我爸种的朝天椒,用柏树枝熏上几天几夜,做成腊肠和腊肉。那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我姐兴奋地打开箱子,一股浓郁的烟熏和肉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客厅。瑶瑶也凑过来,欢呼着:“外婆寄好吃的来啦!”
箱子里塞得满满当当,腊肠、腊肉、风干鸡、还有一大包黑乎乎的干豆角。每一件,都用塑料袋裹了三四层。我能想象到我妈在昏暗的厨房里,佝偻着背,一点一点打包的样子。她总怕寄到常州会坏掉。
我姐的眼眶红了,她拿起一根腊肠,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喃喃道:“还是这个味儿……”
晚上,李浩回来了。看到那箱东西,他也很高兴,笑着说:“爸妈又寄好东西来了,辛苦他们了。”
晚饭,我姐就蒸了一盘腊肠。那味道,霸道地占据了所有人的味蕾。李浩也吃了不少,赞不绝口。我心里的那点不快,也消散了许多。我觉得,或许是我多心了。
然而,第二天发生的事,让我彻底爆发了。
第二天是周末,早上李浩提着一个精致的礼品袋出门,说是去拜访一个朋友。我没在意。中午,我姐在厨房准备午饭,让我去阳台拿点葱。
我走到阳台,一眼就看到角落的垃圾桶里,扔着一个熟悉的泡沫箱。是我妈寄东西来的那个。箱子是空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问正在择菜的姐姐:“姐,妈寄来的东西呢?”
“哦,我分了一下,放冰箱里了。”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走过去打开冰箱,冷冻室里,只有孤零零的几根腊肠和一小块腊肉。大概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
“其他的呢?”我的声音已经冷了下来。
我姐择菜的手停住了。她又开始下意识地摸耳垂。
“李浩……他早上拿去送人了。”她小声说。
“送人?”我感觉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送谁了?凭什么送人?那是我爸妈辛辛苦苦……”
“哥!”她打断我,声音里带着哀求,“你小声点……李浩说,他有个客户是四川人,就好这口。送点过去,拉近一下关系……这叫,这叫人情世こ……”
“人情世故?!”我再也忍不住了,声音陡然拔高,“狗屁的人情世故!那是咱爸妈的心血!他们在家吃什么?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二两肉!大冬天在院子里冻得手通红,给我们熏这些东西!你知不知道那腊肉上的每一道烟熏的痕迹,都是咱爸半夜起来添柴火留下来的!他李浩倒好,拿去当顺水人情了?他有没有心啊!”
我越说越气,一脚踹在垃圾桶上。泡沫箱被我踹翻,滚了出来。
“你个小舅子,你晓不晓得那是我爸妈一根一根晒出来的!”我气得吼出了安徽方言。
我姐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门开了,李浩回来了。他看到客厅的狼藉和蹲在地上痛哭的陈静,脸色瞬间变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和,只剩下冰冷的疲惫。
“你在干什么?”他问。
“我干什么?我问你干了什么!”我指着地上的泡沫箱,怒吼道,“李浩,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你凭什么把我爸妈的东西随便送人?你看不起我们家是吗?!”
李浩没有说话。他走过去,想把我姐扶起来,我姐却打开了他的手。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客厅里只剩下我姐的哭声和我的喘息声。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哥,在你眼里,爸妈的心血是心血。在我这里,一个能救活我公司的单子,也是我全家人的命。”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书房,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愣在原地,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第四章:一扇关上的门,一道裂开的缝】
书房的门关上了,像一道闸门,隔断了所有的声音和情绪。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姐姐。她的哭声也渐渐小了,变成了压抑的抽噎。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李浩那句话,像一把锥子,精准地扎进了我所有愤怒的根源,然后狠狠一搅。
“一个能救活我公司的单子,也是我全家人的命。”
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信息?公司?救活?全家人的命?
我慢慢冷静下来,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扶起蹲在地上的姐姐,她浑身冰凉,眼神空洞。
“姐,到底怎么回事?”我放缓了声音。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个字。良久,她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哥,我们……我们可能要破产了。”
那天下午,姐姐断断续续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李浩的公司,是一家做智能家居的小公司,前几年行情好,赚了点钱,买了这套房子。但从去年开始,市场竞争激烈,大厂下场,他们这种小公司举步维艰。一个大项目被骗,资金链断了,欠了一屁股债。
李浩卖了车,抵押了房子,四处求人,才勉强维持着公司的运转。他每天都在外面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晚上回家,就在书房一根一根地抽烟,整夜整夜地不睡。
他每个月给姐姐的三千块,是他从自己每天吃饭的钱里省出来的。他怕我姐担心,更怕远在安徽的我们担心。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想自己扛下所有。
“他送出去的那些腊肠,”我姐的声音像游丝一样,“是送给那个四川客户的。那个客户手上有个大单子,谈了三个月了,就差临门一脚。李浩知道他好这口,昨天看到爸妈寄来的东西,眼睛都亮了。他说,这是地道家乡味,比任何茅台都有用。”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起李浩这几天的样子。他眼里的红血丝,他紧锁的眉头,他不停敲击方向盘的手指,他接电话时瞬间切换的谦卑语气。
我还想起他带瑶瑶去吃肯德基。或许,那不仅仅是“格局”,更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补偿。他给不了女儿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至少,能给她一个全家桶的快乐。
我以为的那些“不解”,那些“隔阂”,那些“看不起”,原来背后藏着这么一个血淋淋的真相。
我姐还在说:“他也不想的,哥。那天晚上我们吵架,他喝多了,抱着我哭。他说他对不起我,对不起瑶瑶,更对不起爸妈。他说他快撑不下去了……”
我走进厨房,倒了杯水,手一直在抖。
我走到书房门口,站了很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道歉吗?显得太轻了。安慰吗?我有什么资格安慰他?
我轻轻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声音。
我又敲了敲。
“别烦我。”里面传来李浩沙哑的声音。
我没有再敲。我只是靠在门上,轻声说:“李浩,我姐……都跟我说了。”
里面还是一片死寂。
“我不知道……你这么难。”我说,“那包腊肠……送了就送了吧。你要是还需要,我让我妈再寄。她手艺好,熏多少都有。”
我说完,停顿了一下,补充道:“钱……我这里还有点。不多,十几万。是我准备结婚用的。你要是……”
“不用!”门里传来一声低吼,“我李浩还没到要靠大舅子救济的地步!”
我沉默了。我知道,我伤了他的自尊,就像他之前无意中伤了我的自尊一样。我们都是男人,都有自己那点可怜又可笑的骄傲。
我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客厅。
那天晚上,李浩没有出书房。我姐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凉透了,倒掉。
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原来这么难。每一个看似光鲜的表象下,都可能藏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内核。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夜里,我被一阵响动惊醒。我悄悄打开门,看到李浩从书房里出来了。他没有去主卧,而是走进了瑶瑶的房间。
我跟过去,看到他蹲在瑶瑶的床边,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静静地看着熟睡的女儿。他的背影,在黑暗中显得那么孤单,那么沉重。
他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瑶瑶的脸,然后,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耸动。
他在无声地哭。
那一刻,我所有的怨气、不解、隔阂,全都烟消云散。我只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我的妹夫,他不是什么精于算计的常州人,他只是一个在生活的重压下,拼命想保护家人的、普通的丈夫和父亲。
我悄悄地退回房间,眼睛有点酸。
【第五章:一碗没放盐的蛋炒饭】
第二天,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姐姐的眼睛肿得像桃子,李浩一早就出了门,连早饭都没吃。我坐在客厅,看着这个一百二十平的房子,第一次感觉它如此空旷和冰冷。
中午,姐姐在厨房忙碌着。我走进去,看到她在做蛋炒饭。她的动作很慢,有些机械。米饭在锅里翻炒着,金黄的蛋液包裹着每一粒米,很香。
她盛了两碗,一碗给我,一碗给她自己。
我吃了一口,愣住了。
饭,是淡的。她忘了放盐。
我抬起头,看到她也吃了一口,然后就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放下了筷子。眼泪,毫无征兆地,一颗一颗砸在碗里。
“哥……”她哽咽着,“我是不是很没用?”
我放下碗,坐到她身边,轻轻拍着她的背。
“我什么都帮不了他。我只会哭,只会跟他吵,只会给你打电话抱怨。我看着他那么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做不好……”
“姐,你别这么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把瑶瑶教得这么好。你已经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了。”
“后盾?”她自嘲地笑了笑,“我算什么后盾?我只是他的负担。如果不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他可以活得更轻松。他可以不用那么拼命,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喝到胃出血……”
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忽略的,我姐的痛苦。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没钱花,不是因为丈夫不体贴。而是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深爱的男人在悬崖边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无力感,比贫穷本身更折磨人。
她嫁到常州,远离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李浩就是她的全部。当她的全部开始崩塌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崩塌。
“哥,你说,我是不是错了?”她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上写满了迷茫,“当年,要是我听爸妈的,不嫁这么远,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
我看着她,想起了五年前,她跪在堂屋里的样子。那么决绝,那么勇敢。
我摇了摇头,认真地对她说:“姐,你没错。你只是选择了一条比较难走的路。但路难走,不代表是错的。”
我拿起她的碗,走进厨房,从橱柜里拿出盐,均匀地撒在蛋炒饭上,又滴了几滴香油,拌了拌,重新递给她。
“尝尝。”
她接过碗,迟疑地吃了一口。
“生活就像这碗蛋炒饭,”我说,“有时候忘了放盐,就淡了,难以下咽。但没关系,我们把盐找回来,加上去,它就又有味道了。盐,我们家有的是。”
姐姐看着我,愣了很久,然后,她把头埋在碗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流泪。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咸的一碗蛋炒饭。
下午,我给妈打了个电话。我没说公司的事,只说常州这边猪肉贵,腊肠不够吃,让她再做点寄过来。妈在电话那头高兴地答应了,还一个劲地问李浩和瑶瑶爱不爱吃。
挂了电话,我对我姐说:“姐,下次爸妈寄东西,你留一半下来,我们自己偷偷吃。剩下的一半,让李浩拿去做他的人情。”
我姐看着我,破涕为笑。
那个笑容,虽然还带着泪痕,但比我刚来时看到的任何一个笑容,都真实。
晚上,李浩很晚才回来,一身酒气。他没说话,径直走回房间。过了一会儿,我姐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醒酒汤进去了。
我没有去听他们说了什么。但我知道,那扇关上的门,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阳光,总会照进去的。
【第六章:一张被揉皱的卡】
隔天,我跟姐姐说,我要回去了。
她愣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我送你。”
李浩那天没有出门,他也在家。他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憔悴了,胡子拉碴,眼里的光也暗淡了下去。
我收拾好行李,走到他面前。
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他的身体猛地一震,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
“哥,你这是干什么?”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密码是瑶瑶的生日。”我说,“这里面有十五万。不多,你先拿着应急。算我……算我投资你的公司。”
我刻意用了“投资”这个词。
李浩的眼睛瞬间就红了。他看着那张卡,像看着一块烙铁。他猛地伸出手,抓起那张卡,紧紧地攥在手心,手背上青筋暴起。
“我说了,我不要!”他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李浩还没死!”
“你没死,但你快把自己逼死了!”我也提高了声音,“你以为你一个人扛着就是英雄吗?你看看我姐,看看瑶瑶!你以为你瞒着我们,我们就开心了?我告诉你,我们只会更担心,更难过!”
“你是我姐夫,瑶瑶是我外甥女。这个家,不光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有责任!”
我指着那张卡:“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我姐和我外甥女的。我不能让她们跟着你吃苦。你要是个男人,就把这口气咽下去,把公司救活了,然后连本带利还给我!你要是觉得这是施舍,那你现在就把它扔了,然后继续让你老婆孩子跟着你担惊受怕!”
说完,我不再看他,拉起行李箱,对我姐说:“姐,我们走吧。”
李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紧紧地攥着那张卡,手抖得厉害。卡片在他手里,被揉得变了形。
我和姐姐走到门口,换好鞋,准备开门。
“等一下。”
身后传来李浩的声音。
我们回过头。
他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我面前。他摊开手,那张银行卡已经被他攥得不成样子,像一片皱巴巴的叶子。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哥,”他说,“谢谢你。”
没有更多的言语。但这一声“谢谢”,比千言万语都重。
我看到他的眼泪,从镜片后面滑了下来。这个在我面前撑了这么多天的男人,终于卸下了他所有的伪装。
我姐也哭了。她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李浩。
我转过身,打开门,走了出去。我怕我再待下去,我也会哭。
去火车站的路上,是我姐开的车。李浩没来,他说公司还有急事。我们俩一路都没怎么说话。
快到车站时,我姐突然开口:“哥,其实昨天晚上,李浩跟我说,那个四川客户的单子……签了。”
我愣住了。
“他说,他把那包腊肠送过去的时候,那个王总正在跟他老婆视频。他老婆也是四川人,看到腊肠,就说想家了。王总挂了视频,跟他聊了很久的家常,第二天就把合同签了。王总说,生意是生意,但能把家人的心意看得这么重的人,合作起来,放心。”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那包承载着我爸妈心血的腊肠,真的换回了一家人的命。只是方式,和我理解的人情世故,完全不同。
它不是一笔交易,而是一个共情的触发器。它让一个身在异乡的生意人,看到了另一个异乡人的真心。
车停在进站口。我下车,我姐也跟着下来。
“哥,”她帮我理了理衣领,笑着说,“回去跟爸妈说,我们都好。别让他们担心。”
她的笑容,像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
我点了点头:“好。”
临走前,我还是没忍住,问她:“那三千块……”
她笑了:“李浩说了,从下个月起,给我涨到五千。他说,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不能再委屈我和瑶瑶了。”
我终于也笑了。
【第七章:没有答案的答案】
回程的火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窗外再次变化的风景。那些被切割得整整齐齐的绿色田野,在我眼里,不再是冰冷的精细,而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充满生机的力量。
我想起了我来时的那三个疑问。
第一个,关于三千块的围城。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我姐的贪婪,也不是李浩的吝啬。那是一个男人在绝境中,为家庭撑起的最后一片瓦。瓦片虽薄,但下面,是他全部的爱和责任。
第二个,关于一顿肯德基的“格局”。我现在懂了,那不是懦弱,也不是妥协。那是一个父亲在用自己的方式,教女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如何柔软地生存,如何积攒内心的力量。他给不了她一个象牙塔,便努力教她披上软猬甲。
第三个,关于一包腊肠的“人情社会”。我现在也明白了,那不是看不起,更不是不尊重。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丈夫,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那根稻草,恰恰是来自家乡的、最质朴的温暖,最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渡他上岸。
我带着三个尖锐的问题来到常州,准备兴师问罪。却带着一堆柔软而复杂的答案离开。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道黑白分明的选择题。它是一篇充满了各种注释和补充说明的阅读理解。我们总习惯于用自己的逻辑去判断别人的生活,却忘了,每个人的脚上,都穿着一双别人看不见的、磨脚的鞋。
我在常州的这几天,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牛,用我那套来自皖北平原的、直接而粗暴的逻辑,去冲撞一个由常州水乡的、细腻而隐晦的规则构筑起来的家庭。我差点,把这个家撞碎。
幸好,爱是最好的粘合剂。
我掏出手机,翻开家庭群。我妈发了一张照片,她和我爸正在院子里晒新的豆角,阳光下,他们的白发很刺眼。
我打了一行字,想了想,又删掉了。
最后,我只发了一句话:“爸,妈,姐夫说,他特别爱吃你们做的腊肠,让我问问,明年能不能多做点?”
很快,我妈就回了一串语音,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笑意:“哎哟,爱吃啊!爱吃就好!没问题,管够!让你姐夫和瑶瑶多吃点!”
我看着那条语音,感觉眼睛有点发烫。
我带着三个疑问来到常州,却带着一个答案回去: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而爱,有时候需要拐个弯,才能说出口。
火车缓缓驶入安徽境内,窗外的景色又变回了我熟悉的、广袤的土黄色。
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李浩的公司还需要时间恢复,他们的生活也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我不担心了。
因为我知道,那个家里,有了一个学会拐弯表达爱的丈夫,一个懂得丈夫隐忍的妻子,还有一个开始明白“格局”的女儿。
以及,一个愿意把结婚钱拿出来“投资”的大舅子。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