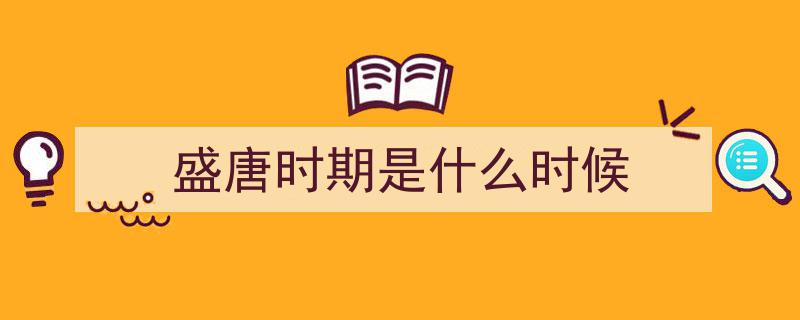盛大的帝国,谁不想沾点光?只是,唐朝到底有多强,有多少人能说清?讲“盛唐气象”,人人都能随口夸几句,真要细数这王朝的威风,不免让人发懵。有人说它能压过三十个国家,吸引得两百多个邦国前来叩门。这听着唬人,但或许只有那些站在边疆看过铁骑踏雪的人,才知道,盛唐的底气是什么。

我有时忍不住琢磨,所谓“汉人武功”,难道真到了唐朝才算极盛?翻书时总是看到,唐军出征,如打春风一样出去了,赢仗却像是家常便饭。130多场大大小小的对外战役,胜七成,听起来像在说别人家的故事,跟咱现在喝茶、吃饭一般平常。
当然,这个“盛”也不是天生的,唐朝的气势,真有过被风吹倒的时候——安史之乱就是个闹心的坎儿。谁都晓得,安禄山、史思明那一伙,把京城搅成了一锅粥。朝堂大乱,战马也似乎无心再往外跑。可是唐朝倒很像那些扛过家庭危机的老人,摔了一跤,但没折了骨头。

那年冬天,长安城里已经断顿了,可郭子仪硬是带着残兵败将,把吐蕃的骑兵撵回了西北。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老将一出手,气场又回来了。安史之乱平了,唐军又开始在四野横冲直撞——说盛唐的武力,是一波一波的气势,不是一锤子买卖。
你要问唐朝到底砸了多少“牌子”,覆灭了多少邻国,老话说三十来家。这三十可不是“市场调查”的数字,是一国一国在地图上消了名字。唐高宗李治那会儿帝国疆域顶峰,据说十二百万平方公里——这跨度有多大,和现在的中国比都还得让步。

李靖出征吐谷浑那一年,风声鹤唳。西北的沙地被马蹄踩得发烫,吐谷浑本是草原上的霸主,和唐朝硬碰硬,结果一年就让大唐收了尾。接着,侯君集挥军西域,顺手把高昌国给拿下了。这几场仗,不只是版图伸展,还给后人立了个“扩张之路”的标杆。
别以为唐人只会往西打,东北边也不甘示弱。公元668年,唐军把朝鲜半岛收拾得服服帖帖。有一年疆域最大,几乎东到日本海、西到帕米尔高原。龙朔年间,那会儿大唐地盘真是“走一步换个民俗”,不知多少小国见了唐使者鞠上躬,自己都感觉像上了大户门。

不过,天有不测,忽然来了个武则天。讲真,这位女皇在后宫吵嚷不是事,偏偏抢了李家的江山,官场风雨连绵不绝。唐朝在武后当政时,忙着内斗,哪能管得了东北那帮新崛起的突厥?于是疆域开始慢慢收缩,像水退了沙滩,边角都露了出来。
但说到底,唐朝的“盛世”是盖章过的。三十多个政权被收编,两百多个国家前来朝贡,这架势,不仅是打赢了仗,也在教世界怎么跟帝国打交道。那时,外邦来朝,有点像现在的粉丝应援,不带点宝贝、礼物可不好意思进城。隋朝就有万国来朝的气派,但真把“朋友圈”做到最大,还得数唐朝。

和唐朝搭上关系的外邦,七十多个像是小弟,有两百多个国家甚至专门给唐皇帝递请安函。朝堂上,老外国王前来谢恩,唐王划好日子,让你排队觐见。要是谁心里不痛快、偷懒不来,那就别怪唐兵敲你后门。这不是外交手腕,是帝国规矩。
关于武则天那根“天枢”纪念柱,还有点闲话。女皇号令全国,召来各国金银宝物,又造了个专属“武周王朝天枢”。这玩意后来给唐玄宗看不顺眼——这孙子可不乐意家门被“篡位史”挂出来。他下令销毁天枢,工匠足足打磨了一个月,那根柱子才算葬进历史。谁知道,或许那时候长安的夜里,有人悄悄看过天枢的影子,一声叹息走远。

其实,唐朝的外交并非咱们现在的互利共赢,讲究的就是“我大唐说了算”。你来我这里是好事,你要敢动歪心思,我就收拾你。不光打人,封官赐物更是不手软。东突厥的阿史那思摩就是个例子,最早是异族贵族,后来投靠唐朝帮忙剿自己老家的可汗。唐王乐了,先封他郡王,又加授武侯大将军。这不光是嘉奖,更像拉拢你做自己人。
这些外邦王公,来了唐朝,能收到丝绸和锦缎,也就有了身份。一匹锦绫不是谁都能往市集一卖的,全靠皇帝赏赐。那些宝贝,不止是财富,更是“你被大唐认可了”。而外邦进贡,也得经过唐朝边境官员层层盘查,防止有邪门玩意藏在礼物里。不小心惊了皇帝,轻则打板子,重的怕是要掉脑袋。

唐朝的盛世,比起咱们今天在教科书里看的那点“辉煌”,其实更杂、更野。外交是压着别人来朝,出征是想打就打,疆域是风吹雨大后的幸存。安史之乱那一摊子事后,唐帝国硬是又熬了百多年。究竟是什么让唐朝这么能撑?是铁马金戈,还是那些边角的小国噤声?
有人说,每一个盛世,背后都有熬过苦水的老兵,也有被忽略的牺牲和误判。唐朝的故事,留给我们的,可能不仅是疆土和威风,还有那些兵荒马乱、权力更替中的人心变迁。盛唐太远了,有时候,咱们更想知道,那些来朝的小国君、被赏赐的异族将军,在夜深时会不会也想家?

盛唐的天边,既有高楼,也有远客。只是,帝国真相到底是什么样?谁能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