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把穆罕默德当成神圣的先知,世代尊崇,可转头就对他的直系后裔下狠手,这事儿听起来挺讽刺的。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部落,可他一走,权力斗争就把他的家族推向深渊。那些高喊“真主至大”的人,手里握的刀却砍向了先知的血脉。
这不光是宗教的分歧,更是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穆罕默德的子孙从阿里到侯赛因,一个个命丧黄泉,留下的教训让人感慨:信仰再纯洁,也挡不住野心的腐蚀。

继承权争夺拉开血腥序幕
穆罕默德在632年病逝于麦地那,没留下明确遗嘱,这直接点燃了继承权的火药桶。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法蒂玛嫁给了堂弟阿里。阿里是最早追随穆罕默德的信徒之一,血缘最近,还在多场战役中立下功劳,比如白德尔战役和乌胡德战役,他都冲在前面。
但穆罕默德刚咽气,阿布·伯克尔就当天被推举为第一任哈里发。这选择靠的是声望和实力,不是血统,把阿里晾在一边。阿里没公开反抗,只是低调过日子,继续传教和务农。
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上台后,阿里还是被排除在外,虽然他偶尔给些建议,但核心权力没他的份。第三任奥斯曼是倭马亚家族的,亲戚当官,腐败问题闹得全国不满。

656年,奥斯曼被愤怒民众刺杀,这给了阿里机会,他终于被选为第四任哈里发。可倭马亚家族不服,尤其是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他是奥斯曼的亲戚,公开指责阿里默许了刺杀。两人打起内战,657年的赛芬战役打得难分胜负,最后仲裁失败,阿里丢了人心。
穆阿维叶趁机扩张,661年阿里在库法清真寺礼拜时,被哈瓦利吉派极端分子用毒剑刺中头部,三天后死去。穆阿维叶顺势上位,建立倭马亚王朝,从共和制转向世袭君主制。先知的家族就这样第一次彻底失去政治主导。
阿里死后,他的长子哈桑短暂继位,但很快让位给穆阿维叶,避免更多流血。哈桑隐居麦地那,669年去世,有人怀疑是被穆阿维叶毒死的。次子侯赛因拒绝向穆阿维叶效忠,继续在麦地那生活。这段继承争端,本质上是部落利益和权力分配的问题。
阿拉伯人尊穆罕默德为圣,可他的子孙成了牺牲品,穆阿维叶这类人为了稳固王朝,不惜用阴谋和武力清除威胁。历史资料显示,阿里一生参与了几乎所有穆罕默德的战役,却在权力角逐中落败,这反映出早期伊斯兰社会从宗教共同体向帝国转型的残酷现实。

卡尔巴拉事件加剧宗派分裂
680年,穆阿维叶死了,他的儿子亚兹德继位,进一步推行世袭制。亚兹德要求全国效忠,侯赛因作为穆罕默德的外孙,公开拒绝,因为他认为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非法,不符合血统和神授原则。
库法城的什叶派信徒写信侯赛因过去,说愿意支持他当哈里发。侯赛因派堂兄穆斯林·伊本·阿基尔先去探路,穆斯林到了库法,集结了不少支持者。但亚兹德派总督伊本·齐亚德镇压了他们,穆斯林被抓捕并杀害。
侯赛因没收到坏消息,就带着家属和72名亲信从麦地那出发,前往库法。途中得知库法变卦,但他没退缩,继续前进。队伍抵达伊拉克西部的卡尔巴拉平原时,被倭马亚军队包围。对方有数千人,先切断水源和粮食,逼侯赛因效忠亚兹德换取活路。

侯赛因不答应,10月10日战役爆发。侯赛因一方只有几十人,很快全军覆没。他本人身中多箭,被斩首,头颅送往大马士革。他的六个月大儿子阿里·阿斯加尔也被箭射死,其他亲信和家属大多战死或被俘。
这场战役不是平等对决,而是单方面的屠杀。倭马亚军队由乌马尔·伊本·萨德指挥,初始4000人,后增援更多。侯赛因的阵亡者包括他的兄弟、儿子和侄子,总数约70人。
战后,幸存妇孺被押送王都,亚兹德在宫中检视侯赛因的首级。这事件直接导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加深,什叶派视侯赛因为殉道者,每年阿舒拉节纪念他的牺牲。
亚兹德这类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不惜杀害先知后裔,这在历史上被视为伊斯兰的原罪。卡尔巴拉不只是战场,更是权力野心吞噬信仰的象征,阿拉伯人一边奉穆罕默德为圣,一边让他的血脉断绝在沙漠中。

阿拔斯王朝的清洗延续迫害
卡尔巴拉后,倭马亚王朝没马上崩盘,但内部矛盾积累。什叶派力量转入地下,传播阿里血统的合法性。750年,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他们出自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家族。
他们起初和什叶派联盟,宣传替阿里后裔复仇。革命从呼罗珊开始,阿布·穆斯林率军西进,在扎布河战役击败末代哈里发马尔万二世,马尔万逃亡埃及被杀。
阿拔斯上台后,迁都巴格达,本以为什叶派能迎来复兴,可他们很快翻脸。阿拔斯王朝排斥阿里一系,坚持自己的统治合法。什叶派强调只有阿里后裔才是伊玛目,这威胁到新王朝。
结果,阿拔斯开始镇压曾经的盟友,侯赛因的后代被通缉和暗杀。762年,曼苏尔镇压阿里德叛乱,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在麦地那起事,被军队围捕斩首。他的兄弟易卜拉欣在巴士拉续战,也中箭身亡。

哈伦·拉希德时期,继续压制什叶派,监禁伊玛目穆萨·卡齐姆,在监狱中下毒致死。马蒙一度任命阿里·里达为继承人,试图和解,但阿里·里达途中中毒身亡,政策逆转。
穆塔瓦基勒统治下,847年起迫害加剧,拆毁侯赛因陵墓,禁止朝拜。阿里后裔流亡,藏身山区或改名换姓。什叶派发展出第十二伊玛目隐遁的理论,认为他会再临,这成了他们的核心信仰,也为伊朗的宗教体制打下基础。
穆罕默德的子孙在王朝更迭中反复被利用,用完就扔。阿拔斯王朝扩张到北非和西班牙,可对先知血脉的清洗没停过。
这反映出中东政治的现实:宗教往往是权力的工具,阿拉伯人尊崇穆罕默德,却让他的后裔成为政敌的靶子。历史上,这样的迫害持续千年,影响至今的中东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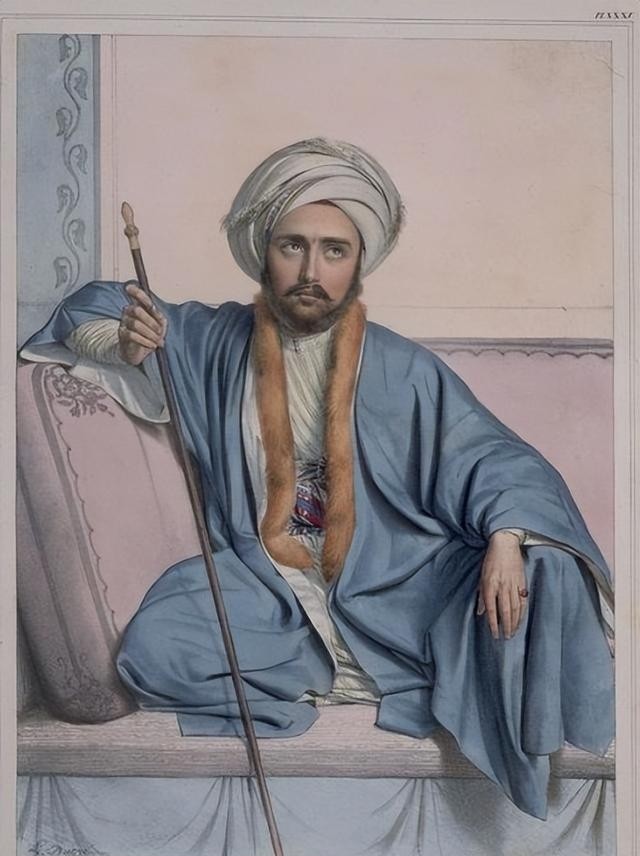
穆罕默德子孙的遭遇不光是历史旧账,还直接塑造了中东的宗派格局。什叶派从卡尔巴拉事件中汲取教训,强调殉道和反抗。
伊朗萨法维王朝在16世纪推广什叶派为国教,进一步强化了分歧。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如沙特,视什叶派为异端,双方在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的冲突中反复上演旧恨。
侯赛因的后裔虽没重获权力,但成了象征。什叶派在伊朗和伊拉克有影响力,可在逊尼派主导的地区仍受压制。阿拉伯人一边在清真寺颂扬穆罕默德,一边在政治中延续对他的血脉的排挤,这矛盾根深蒂固。
历史事实证明,信仰的裂缝一旦形成,就难愈合,中东的动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想想看,先知统一了阿拉伯,可他的子孙却在同胞刀下凋零,这事儿多荒唐,却又是权力斗争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