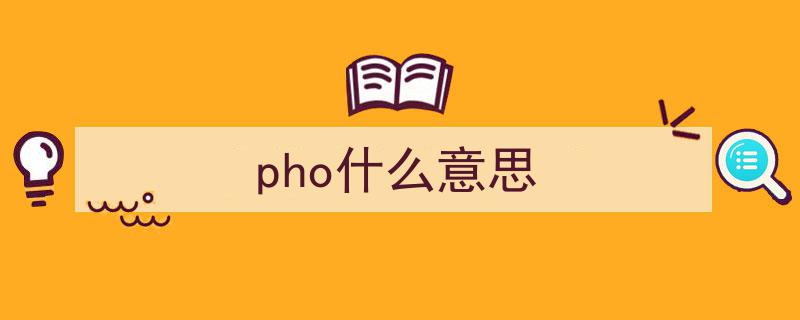▞
以“细末”指称的面食:馍馍与饽饽 面条是最常见的面食,它的名称就是食材与形制的结合。“面”,东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麦屑末也”,此义相当于今天的“面粉”。在北方方言中,“面”还多保留此义,而长江流域以南,单说“面”主要指面条。这种省略法,在南方方言中还有平行的例子,就是“粉”。“肠粉”是“肠粉馃”的省略,“米粉”是“米粉条”的省略。此类影响远播域外,越南的“pho”就是粉条。 “面”与“粉”都是“细末”的意思。而以“细末”作为面食的指称,还有两个常见的名称,但一般大家都意识不到这可能与食材本源相关:馍馍与饽饽。馍,在很多地方都是指无馅的馒头,但有些方言中“馍”可用为面食总称,比如河南地区常见的食品“烙馍”其实就类似山东的煎饼,徐州方言“馍馍”可指馒头、烙馍、卷子、油饼多种食品。清代方外山人《谈徵》中说:“京师及河南人谓饼曰
 。”“
。”“  ”是“馍”的异体写法。方外山人所说的“饼”,是古汉语中对面食的总称。可见清代的北京话里“馍馍”也是面食的泛指。可能经由蒙古人的传播,“馍馍”一词传入西藏及尼泊尔等南亚地区,而当地的“馍馍”就是小肉包。
”是“馍”的异体写法。方外山人所说的“饼”,是古汉语中对面食的总称。可见清代的北京话里“馍馍”也是面食的泛指。可能经由蒙古人的传播,“馍馍”一词传入西藏及尼泊尔等南亚地区,而当地的“馍馍”就是小肉包。 
 ”大约都是在元代的文献记录中才开始普遍出现。元代与关汉卿同时的杨显之在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写道:“你两个且起去揩了泪眼,我买馍馍你吃。”“馍”的词源可能就是“末”,“末”本是中古时期的入声字,而北方大部分方言在宋元时期入声就消失了,古人不明语源,于是就依音近的声旁造出了“馍”字。 “饽饽”与“馍馍”音义都接近。“饽饽”的名称在元代马致远的杂剧《邯郸道醒悟黄粱梦》里就有出现:“他怀里又没点点,与孩儿每讨饽饽。”清代翟灏在《通俗编·饮食》中说:“饝饝,即波波。”在清代,饽饽也是面食的统称,《清稗类抄·饮食》中也说:“饽饽,饼饵之属,北人读如波波,不读作勃字之本音也,中有馅,一作饝饝。”满族人从汉语中借了“饽饽”一词,清代宫廷正月初一吃“煮饽饽”,其实就是饺子。 “饽”与“末”有意义上的关联。唐代陆羽《茶经》里说:“凡酌置诸碗,令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陆羽所说,本来指茶汤上的泡沫,《茶经》中的“饽”,也可以写作“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没沦别无期。”“白勃”就是水浪在滩岸上留下的泡沫。在南北朝时,“勃”不光指泡沫,也有粉末的意思。北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详细的“饼法”的记载,都是关于当时白案面食制作的一些说明,比如“餢 ”条下曰:“干剂于腕上手挽作,勿着勃。”面剂子用勃,就是擀面时防粘案板而加的粉,至今许多方言还保留同样的说法。
”大约都是在元代的文献记录中才开始普遍出现。元代与关汉卿同时的杨显之在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写道:“你两个且起去揩了泪眼,我买馍馍你吃。”“馍”的词源可能就是“末”,“末”本是中古时期的入声字,而北方大部分方言在宋元时期入声就消失了,古人不明语源,于是就依音近的声旁造出了“馍”字。 “饽饽”与“馍馍”音义都接近。“饽饽”的名称在元代马致远的杂剧《邯郸道醒悟黄粱梦》里就有出现:“他怀里又没点点,与孩儿每讨饽饽。”清代翟灏在《通俗编·饮食》中说:“饝饝,即波波。”在清代,饽饽也是面食的统称,《清稗类抄·饮食》中也说:“饽饽,饼饵之属,北人读如波波,不读作勃字之本音也,中有馅,一作饝饝。”满族人从汉语中借了“饽饽”一词,清代宫廷正月初一吃“煮饽饽”,其实就是饺子。 “饽”与“末”有意义上的关联。唐代陆羽《茶经》里说:“凡酌置诸碗,令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陆羽所说,本来指茶汤上的泡沫,《茶经》中的“饽”,也可以写作“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没沦别无期。”“白勃”就是水浪在滩岸上留下的泡沫。在南北朝时,“勃”不光指泡沫,也有粉末的意思。北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详细的“饼法”的记载,都是关于当时白案面食制作的一些说明,比如“餢 ”条下曰:“干剂于腕上手挽作,勿着勃。”面剂子用勃,就是擀面时防粘案板而加的粉,至今许多方言还保留同样的说法。 ▞
从“浙中无麦”到烧麦北上 “面、馍、饽”都是对麦粒磨成细末后的不同称呼,是面食的基本材料,因此可作为面食的通称。比起这些词来,面食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质料——“麦”。 “麦”也可以用来表示面食,不过这种用法主要保留在长江以南的方言区。比如吴语温州话、客家梅州话中,“面粉”被称为“麦粉”。梅州话把用面粉做的糕点统一称为“麦粄”,而吴语的金华、台州等地把面粉做的烧饼称为“麦饼”,上海崇明话叫“麦烧饼”,杭州则称为“麦乌烧”,温州还有一种面条被称为“麦条儿”,台州还有一种面疙瘩因外形像虾,被叫作“麦虾”……这些称呼其实反映的是古代南方地区原来不流行面食的历史。北宋时苏轼还称“浙中无麦”,麦作在长江以南流域的推广据研究是从南宋开始的,所以南方方言中对于面食相对比较陌生,就使用原作物“麦”来直接称代了。 但这种带有地域性的“麦”通过一种面食被带到了大江南北,那就是“烧麦”。“烧麦”在各地有不同的写法:烧卖、捎梅、稍美……写法各异,其实都是“麦”字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变化。 “麦”是中古入声字,到宋元时入声消失,在各地方言中产生了读音差异。像武汉、上海、山西等地方言中,“麦”“卖”两字读音不同,而“烧麦”一般都从“麦”的读音。(广东例外,广东点心的“烧卖”应当是后来传入,便照传入时的写法读“卖”。)武汉话的“麦”就音近于“梅”。元末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中就有“稍麦粉汤”和“素酸馅稍麦”的提法,均写作“麦”字。而“烧”字,只是表示熟食的意思而已,与“烧饼”“烧鸡”并无二致。 有文章认为烧麦是蒙古语借词,蒙古语的“suumai”意思是没有冷却的面食,这看来是倒果为因,当是蒙古语从汉语借入了“烧麦”,蒙古语的意思完全对应汉语“烧麦”的字面意义。▞
炊饼、胡饼和饼饼面 前文已经提过,“饼”是古汉语中面食糕点的总称,它比“馍、饽、麦”更为古老。《汉书》就已经提到汉宣帝在民间时常出入饼肆,据此“饼”在西汉时就已经开始流行。《说文解字》中说“饼,面餈也”。“餈”是用大米或小米制成的糕点,今天方言中的“糍粑”的“糍”就是“餈”的新写法。 《世说新语》中说三国时的美男子何晏皮肤白,魏明帝曹睿想知道何晏是不是脸上搽了粉,就让他在六月暑天吃热汤饼。汤饼,就是煮面片或者面条一类的带汤面食。何晏吃得满头大汗,“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吃热面条发汗,今人犹是如此。 晋初何曾生活豪奢,“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蒸饼,就是起酵的实心馒头,“坼作十字”就是今天所谓“开花馒头”。据说到了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桢的讳,“蒸饼”改名为“炊饼”,所以《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炊饼”其实是山东大馒头。记得八十年代山东电视台拍的电视剧《武松》,“炊饼”的道具做成了今天烧饼的样子,后来央视版《水浒》就仔细地改成了馍馍、馒头。
▞
日本乌冬与中国馄饨 与“饼”的意义理据相似的面食名称还有“馄饨”。作为遍及海内的大众食品,“馄饨”的语源也跟烧麦一样,异说叠起。有说是象征包罗万物的“混沌”,如王谠《唐语林》云:“馄饨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书浑沌,从可食矣。”又有认为“馄饨”本为外来语,李匡乂《资暇集》说:“世言馄饨是塞外浑氏屯氏为之。”今人又有根据异体形式“云吞”以为是皮薄如云霞而吞食,或者又依馅料多种多样认为是“混众物而吞之”。这都是望文生义。 “馄”和“饨”本来都是面食通名。西汉扬雄《方言》卷十三记载:“饼,谓之饨,或谓之餦、馄。”此处的“饨”,本作“饦”,经钱绎、周祖谟等考证当为“饨”字。从意义上看,“馄”本义应是“混合,混同”,《老子》十四章“故混而为一”,河上公注云:“混,合也。”而“饨”,本义应是“屯聚”,《广雅》云:“屯,聚也。”两字本义,与“饼”表“合并”异曲同工,原来都是表示“和面”的基本操作工艺。今天汉语中的“馄饨”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是薄皮带馅连汤食用的,但也有极少数方言中有不一样的意义。比如山西万荣方言中,馄饨既可以指一种圆形薄皮的水饺子,又可以指形状多样的花馍,而且制作的场合也一般较隆重,都是用于敬神、待客或馈赠亲友。 日语中的“乌冬”,根据日本美食家本山荻舟《饮食事典》的说法,就是从“馄饨”的说法辗转音译而成的。一般人很难理解日本乌冬是一种面条,怎么会跟中国带馅的“馄饨”扯上关系。南北朝末年的颜之推已经提到“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从样子描述看,基本就是今天饺子的模样了。但从扬雄到颜之推,也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跨度,更何况在西晋《饼赋》中也未明言“馄饨”,只提到“牢丸”,有观点认为可能是馄饨、汤圆一类的食品。 而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方》卷二十五中云:“赤石脂捣作末,和面作馄饨,空腹服一碗以下,不过两顿瘥,老人尤佳。”赤石脂就是红高岭土,既是捣末和面,定不可能是作馅心。又同卷云:“干姜(末)熟艾上二味等分,作面馄饨如酸枣大,煮熟,服四五十枚,日二服。”此处的“面馄饨”说得更明白,就是类似今天的面疙瘩。可见唐代人所谓的“馄饨”未必有馅。而日本把“乌冬”当作“馄饨”之流变,也就未足为奇了。 古今食品同名异实的现象本来就十分普遍,比如南北方的馒头,有馅无馅,迥然不同;即便在同一方言中,也会因为方言时代层次的差别造成同名异实,比如扬州地区,馄饨和水饺形制截然不同,然而扬州早茶有“饺面”,其中的“饺”实际是馄饨,“饺面”其实就是广东的馄饨面。本来与“饼”同为面食通称的“馄饨”,在中古时代已经形成了地域指称的差别,即便是颜之推这样的通才,也未必对市井俗语的名实有全然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