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凌晨,太原城外的炮声像催命鼓一样,一阵紧似一阵。
阎锡山坐在绥靖公署后楼的小客厅里,面前一盏汽灯把脸色照得蜡黄。

他已经换掉了中将军装,穿起青布长衫,袖口磨得发亮——这身衣服是“五姑娘”半个月前亲手给他缝的,针脚细密,领口还绣了一朵小小的白梅。
此刻,他捏着电报稿纸的手却抖个不停,纸上那几行字像钉子一样钉进眼里:
“妹虽女流,死志已决……今生已矣,一别永诀。”
落款,是“五姑娘”阎慧卿。
他猛地抬头,窗外火光冲天,曳光弹划破夜空,像除夕的焰火,却带着死亡的味道。
副官第三次催他动身:“主任,飞机在汾河西岸等,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阎锡山张了张口,嗓子却像被棉花塞住,只挤出一声嘶哑的“走”。
他终究没有回头,脚步踉跄地穿过黑漆漆的走廊,楼梯口那只铜痰盂被踢翻,咣当一声滚下台阶——那是五姑娘怕他咳血,特意从天津法租界带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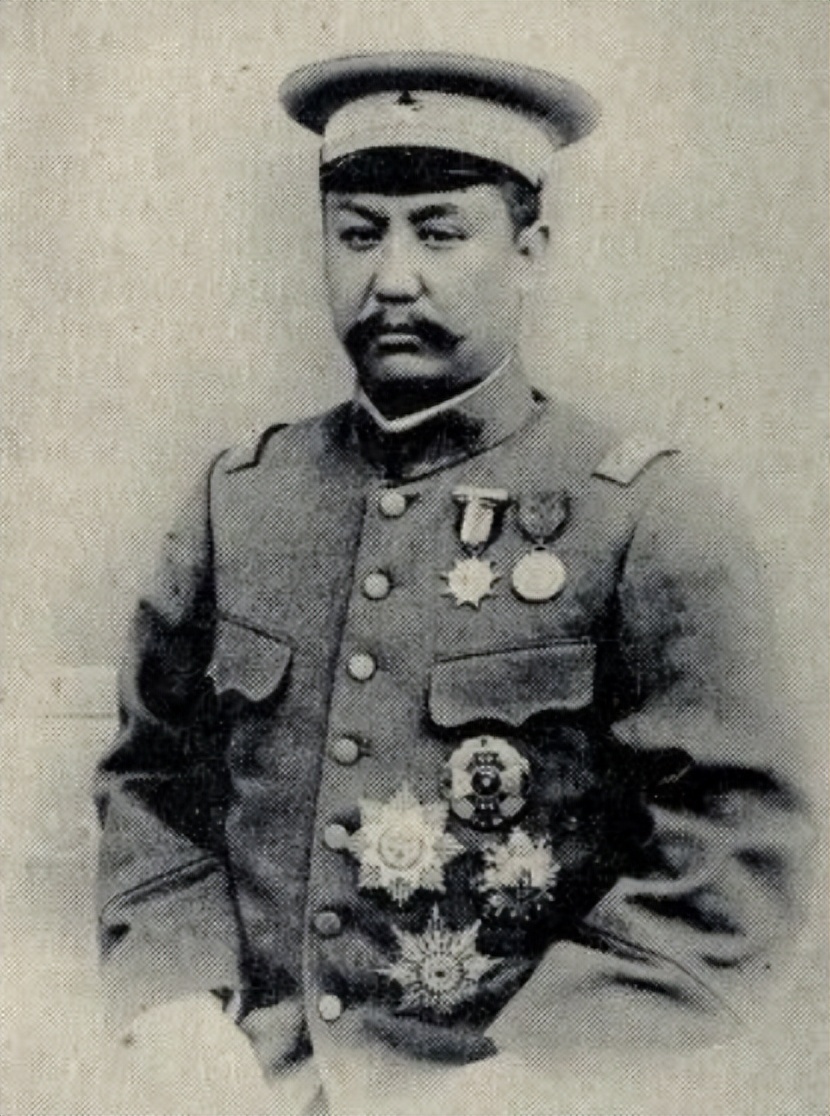
一小时后,C-47运输机的螺旋桨卷起黄尘,载着这位统治山西三十八年的“土皇帝”仓皇南去。
他坐在舷窗边,脸贴冰冷玻璃,看着太原城一点点被硝烟吞噬,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也是四月,五姑娘穿着月白短褂,在河边给他摇杏树,花瓣落了她一身。
那天她笑得像只刚出壳的云雀,说:“大哥,你若能一直当山西的家,我就一直给你摇杏花。”
机舱里灯光惨白,副官递来一杯威士忌,他摆摆手,只把电报折成四四方方一小块,塞进贴身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那封电报后来被他带到台湾,锁在士林官邸的抽屉里,钥匙再没拔出来过。
“五姑娘”到底是个什么人?太原老人至今提起来,还会压低嗓子,像怕惊动什么。

阎慧卿并非亲妹,是堂叔那一支的闺女,因排行第五,被府里上下叫“五姑娘”。她十四岁进督军府,先伺候老太太,后来老太太瘫了,她就挪到外书房照顾阎锡山。
阎锡山夜里批公文,她在一旁剪灯花;他胃寒,她把红枣烤得焦黄,用帕子托着,一粒粒剥给他;他发脾气摔了茶碗,她蹲下去一片片捡碎瓷,手指割出了口子,血滴在青砖地上,像点点红梅。
久而久之,督军府里有了闲话。
副官们半夜换岗,常见五姑娘披件狐肷斗篷,从阎锡山卧室出来,鬓角汗湿,脸颊却像抹了胭脂。
1935年,阎锡山元配徐竹青病逝,太原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说五姑娘要扶正。

可他没松口,只让她搬进后罩房,门口添了两个卫兵,说是“保护”,更像一道锁。五姑娘倒安静,每日抄《金刚经》,字迹娟秀,像一串串小燕子。
1948年晋中战役惨败,太原成了孤岛。阎锡山脾气愈发古怪,每晚要五姑娘陪着喝汾酒,喝醉了就骂“徐向前欺我太甚”,骂着骂着,头枕在她膝上睡去。
她轻轻抚他花白头发,像抚一只受伤的老狼。
有天夜里,她突然说:“大哥,若太原守不住,我陪你殉了也罢。”阎锡山愣了半晌,只当她小女儿情态,一笑了之。
1949年3月,南京派来飞机接要员,阎锡山却迟迟不走。他在等美国人调停,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等一个奇迹。
直到4月20日,东山牛驼寨失守,城外制高点尽失,他才慌了。
21日晚,他召集亲信开会,决定分批撤退。五姑娘给他收拾细软,把金条缝进棉袄夹层,把蒋介石送的勃朗宁擦得锃亮。

她以为会带她走,可阎锡山只说:“你留下,替我守着家庙。”轻飘飘一句,像掸掉袖口灰。
五姑娘没哭,只问:“那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阎锡山背过身,声音像砂纸磨过:“快则十天,慢则半月。”她点头,福了一福,退到屏风后。屏风上绣着喜鹊登梅,她伸手摸了摸,指尖冰凉。
22日,阎锡山飞离太原。24日凌晨,解放军攻入城。
五姑娘换了件藕荷色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坐在督军府西花厅。桌上摆着四样点心:豌豆黄、驴打滚、玫瑰饼、桂花糕,都是阎锡山爱吃的。
她斟了两杯汾酒,一杯敬天,一杯自己慢慢喝了。
随后,她走进内室,反锁房门,划着火柴,先点着了床上的锦被,又点着了堆在墙角的书信——那是阎锡山三十年来写给她的,从“吾妹见字如晤”到“卿卿如晤”,一封没落。
火舌舔上窗棂时,她躺在那张雕花木床上,怀里抱着阎锡山送她的德国蔡司相机——1937年忻口战役前,他给她拍的最后一张相片:她站在黄河铁牛旁,风吹起刘海,笑得见牙不见眼。
她轻声说了句什么,被火焰噼啪声盖过。据后来冲进来的女佣说,她嘴唇形状像是“大哥”。
太原解放后,军管会清点阎府遗物,在废墟里扒拉出一具焦黑女尸,腕骨上还套着只翡翠镯子,翠绿得刺眼。
因无法辨认,就地葬在双塔寺公墓,连块碑都没立。后来修烈士陵园,坟平了,种上一排白杨。
白杨成林那年,阎锡山在台北阳明山写了首诗,末两句是“孤魂夜夜双塔雨,不见并州旧杏花”。写罢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海峡那边,他再没提过五姑娘。只是每年清明,士林官邸后山会多出一只小小锡箔元宝,被雨水打成灰白色。
